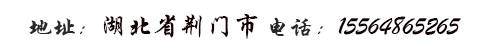焦点朱凌飞曹瑀景观格局一个重新想
|
本文来源于《思想战线》年第3期第42卷,作者:朱凌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曹瑀(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建筑学系研究生)。 对生态环境的描述是民族志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但其不应仅仅为文化事项的呈现提供一个“背景”,也不应局限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工具。景观人类学的研究,为我们思考社会关系与物质空间的共生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而因这种关系的差异性所体现出来的空间秩序,则形塑了“景观格局”,为我们重新想象乡村社会文化空间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而芒景布朗族村不同层级的景观,为我们的“想象”提供了实在的证明。 一、民族志中的“空间”维度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总在某一特定的时空——田野点(fieldsite)之中展开,这一客观存在的,但却是被生活于其中的人群所界定的物质环境,对他们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人类学家的笔下,对“生态环境”的呈现似乎已经成为“标准”民族志的必备要素,除了为文化事项的展现提供必需的背景之外,也有发掘物质环境与社会建构之间关系的目的。 我们看到,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特罗布里恩德岛人关于库拉的神话时,就曾试图揭示土著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生存的世界,于是,“我经常描述自然环境,目的不只是使叙述生动,或让土著的风俗更加直观,而是要展示土著人如何认识他的行为所发生的环境,并试图描绘环境给他的印象和感觉,使我得以理解他的民间故事、他在家里的言谈,以及他在这些环境下的行为”。[①]对读者而言,马林诺夫斯基对自然环境的描述,使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一系列库拉行为有了想象的空间和色彩,使文字具有丰富的画面感,也就使人类学的研究可视化了。列维-斯特劳斯也曾试图通过对村落格局的研究,发现波洛洛印第安人的神话、制度和宗教体系得以存在的依据,于是“我们整天从一间房子走到另一间房子,普查住在里面的人,弄清楚他们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用棍子在地面上做记号,把村子按照不同的权力地位、不同的传统、不同的阶层分级、责任与权利等等假想的划分线划分出来,成为几个不同的区域”。[②]于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村落结构图就不再仅仅是平面的几何图形,隐藏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也逐渐呈现出来。为了描述19世纪巴厘的地理与权力制衡之间的关系,格尔兹对南部巴厘的地形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并引导读者“站在火山斜坡面朝大海”或者“站在海岸面朝山坡”来观察,可见“整个地区并不仅仅呈现为纸盒似的维度,它还被众多深不见底的河流峡谷所切分,这些河谷从山脉上面一直延伸到海边,将整个南部灌溉水系切分成一组细小的、馅饼状的长条”。并就此判断,“就国家组织而言,这种地形易于建立一种纷繁复杂、非单一化的地理政治力量场域,而其政治活动当然绝不会是统一的”。[③]而“面向海洋的君主”和“面向山脉的君主”之间的权力竞争,更说明了巴厘政治“土地几何学”的特性,使景观的政治属性展露无遗。最为直接的是,沙伦·特拉维克索性以“导游”的方式,带领读者参观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包括地理位置、周边环境以及各种类型的办公室和实验室等,甚至还有路边的告示牌、墙上的照片、书桌上的摆设。[④]这种景观的描述,不仅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且更重要的是,将身处其中某一位置的科学家、行政人员、勤杂工等的特定行为方式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一一呈现出来。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让我们看到,人类学家对客观环境的描述,其意义在于探讨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在特定环境的规约之下,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关系,但似乎也就仅止于此。这不禁让人质疑,某一人群生存的物质环境是先验地存在的吗?如果没有这一空间,人们在哪里活动并建构起某种社会关系?而空间的存在,不也必须是被特定社会关系所连接起来的一群人在活动中所建构的吗?在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看来,“空间”不应只是充当一种辅助物或背景,它本身就是主角,空间是可以将经济、政治、文化子体系重新加以辩证整合的一个新视角。[⑤]社会关系不仅是在特定空间中形成的,而且是与这一空间同时产生,并同时发生改变的。 二、景观人类学与村落视野中的“景观格局” 年6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召开“景观人类学”学术会议,并出版论文集《景观人类学:关于场所与空间的观点》。“景观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由此而得以逐渐成形。在该书导论中,赫希(EricHirsch)将外部观察者所观察和描述的图景称为“空间”(space),而将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基于知识、经验和观念所形成的场域称为“场所”(place),此两者可分别被视为景观的“前景”(foreground)与“后景”(background),分别具有实在性(actuality)和潜在性(potentiality)的特征。因而,“景观”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也即“我们最初看到的景观和当地人在实践中形成的景观,而后者是需要我们通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描述和阐释才能意识到并逐步理解的”。[⑥]随着此类民族志案例的不断累积,景观人类学的研究范畴被概括为聚落生计方式与景观的互动、景观符号、记忆与认同、神圣空间与仪式信仰、社会组织结构与景观秩序等,并逐渐涉及到本土性与传统、移动性等研究议题。[⑦] 人类学视野中的“景观”,在“景致”“景象”等字面上“自然环境”的意义之外,更需融入“人”“社会”“文化”的视角,由此便在其中嵌入了“历史记忆”“社会网络”“身份认同”“地方性知识”等方面的要素。基于此,笔者尝试对这一分支学科进行初步的界定。即景观人类学是,利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某一人群在其生存的客观环境中所形成的知识、情感、制度、行为等进行的研究。其中,当地人通过不同的活动与其生存环境所建立的关系是关键要素,而“关系”也必然是以不同的模式存在的。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意在描述中国社会结构中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象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⑧]。很显然,费孝通以“涟晕”的形象将“差序格局”理论可视化了。其启示意义在于,一个当地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是否也如此种“涟晕”一般,有远近亲疏之分,而如果空间(景观)又是由关系所构成的,那么是否存在一种不同层级的“景观格局”?如此一来,人与物质环境的“心理距离”与“空间距离”将可建立起一种正相关的联系。 在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中,“景观格局”一般指景观的空间格局(Spatialpattern),是大小、形状、属性不一的景观空间单元(斑块)在空间上的分布与组合规律,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在看似无序的景观中发现潜在的有意义的秩序。[⑨]景观生态学更多中科治疗白癜风有疗效北京中科医院爆光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feizhouxiangdx.com/jdhzp/911.html
- 上一篇文章: 收藏花农绝不外传的8个养花绝招,99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