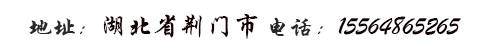六神无主
|
六神无主 老孙还是小孙的时候刚搬来弄堂,隔壁商户的儿子正往外搬花,一盆盆的水仙,香得扑鼻。 他吸了两口,乐了,问是什么花。 于是他的小店就叫水仙按摩馆。 写招牌的就是那花店搬花的儿子,大学生,送牌子来的时候还端来一盆水仙,跟蒜似的,还没泄露香味。 “您再等等就开了。”那大学生大声地说。 他用手小心地碰了碰水仙,摸了摸娇嫩的骨朵儿,也大声地说谢谢。 “呀,就算我是真瞎子,也不是耳朵不好使。”他扶了扶墨镜心想。 “真烦人。” 邻里之间都可怜年纪轻轻就瞎掉的小孙,平时也乐意照顾他的生意。他门上挂了一只鼓鼓的像水仙球根的铃,来人了就会尽职地响起。 闲时,他就窝在竹椅上晒太阳,离远了一看像是窝在花丛里——门口的水仙还是开花了。毕竟春天都快结束了,再倔强的水仙也不得不开花,再不开花花季就要结束了。 路过的街坊看见了,都噗呲一声笑出来, “原是史湘云醉卧芍药,我们这有小孙师傅仰躺水仙。”笑过之后又觉得可惜,可惜他看不见。 小孙安心地从墨镜里窥探世界,水仙嫩黄嫩黄的,抖落一身水珠,隔壁的花店又新进来许多花,都没有水仙那么娇憨可爱。 他视线又飘到那边的商户,门口放着的是翠绿翠绿的迎宾竹,挂着几个小小的金元宝,褪了色的角是廉价的土黄色。阳光照在新安的玻璃上,印出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他正着数了三遍又反着数了三遍,然后直到太阳不再放映这色彩,他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 他游刃有余地扮演着盲人的角色,养有脾气的水仙、伺候对他颇为友善的邻里的背和颈椎。 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不得不带着这副墨镜,所以一切色彩都抹上了暗色的阴影,可是生活就是这样,小孙心想,做人要从一而终,既然要做个盲人按摩师就要一直带着这副眼镜。 从这副眼镜里,他看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世界,那些来按摩的客人会因为他的眼盲而变得松懈,他们不再伪装,变得轻松,做着一些无伤大雅的小动作,虽然小孙能看到这一切,但他很乐意保守这些秘密。 街坊们也担心小孙一个人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但是这个担心很快就因为另一个人的到来而消失了。 阿仙来的那天打了一把塑料伞,小孙记得很清楚,陆城虽然喜欢在春天下点小雨,但是很久没下过那么大的雨。 她披着一件鹅黄色的开衫,举着伞,提着包,从张家烧鹅那边慢慢地走过来。雨水顺着伞沿滴滴答答,她的影子像是浮在浅浅的积水里,薄薄一层,像人一样轻飘飘的没有实感。 影子的轮廓是一个巨大的伞头和罩在里面的细小的腿,看上去像一只蘑菇。 对,一只新鲜的湿润的蘑菇。 年的雨水淋湿了小孙的心,滋养着他的心房,长出了一只蘑菇。 在水汽晕染的橙色灯光的掩护下,她站在路那边走进了一家小旅馆,第二天这条巷子都知道来了一个美丽的哑巴。 街坊们有意为她找一份工作,思来想去就把她带到了水仙按摩馆。没人知道她的来历她的名字,她只是温和地笑着,微微低着头,含着下巴,然后证明她会做饭会洗衣服会干活。 也许美丽本来会伤害她,可是哑病却让她获得理解和怜爱。 小孙留下了她。 他们刚开始的交流方式是小孙说同意就叩一下桌子,不同意就叩两下。 “我给你起个名字吧。”小孙说,“我们这是水仙按摩馆,你就叫阿仙吧。” 她笑了,点了点头,又想起了小孙看不到,就曲起手指叩了一下桌子。 小孙觉得好笑,其实自己什么都看得见,偏偏要这样费劲地和阿仙交流。 虽然阿仙是说不了话的,但是确实让小孙的世界热闹起来了。她笑着接待每一位客人,因为她无法说话,来客也就没法问出难堪的话题。 她搬着大盆坐在门口台阶揉搓衣服,扬起的水珠滴答进水仙的盆里。 小孙再也没有在门口晒过一下午太阳,他就坐在屋里看向屋外发呆的阿仙。 只有小孙在屋里的时候,阿仙才不再摆着一张笑脸,总是抿着嘴唇,显出一层淡淡的忧伤。小孙猜想她并不快乐,可是他又无法开口询问——因为他看不到她的表情,而她也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在这里待了几个月,阿仙学会了盲文,那些布满点点的小纸条四散在按摩店里,像是某种隐秘的密码,传递着不为人知的信息。 其实那都是一些很稀疏平常的话。 “今天吃角瓜好吗?” “好的。” “今天要换床罩吗?” “要,麻烦了。” “又接了三摊生意。” “知道了。” 后来也会聊一些话,点数就更密集了一点。 “昨天晚上忘记搬水仙了,盆里的水都涨了。” “最近菜场的菜很贵。” 小孙突然很感谢自己是一个装盲的人,因为话语只会在脑海里停留,然后被时间吹得模糊,但是盲文会被永远的留在纸上,像正在播放的留声机,像按下快门的照相机。 对于小孙来说,日子就像盲文,越过越稠,那些黑点,像东头女儿家脸上的雀斑,像西街老头下棋的棋子,是阿仙嘴角的痣,是水仙花粉闪闪烁烁。 黑点在纸上以某种规律下了一场雨,陆城也下着一场小雨。 那一天小孙在纸上写, “想不想听听音乐?” 隔壁的大学生借他收音机和磁带作为按摩的报酬,他用眼睛看过是很适合现在播放的歌。 阿仙立马起身去打开,然后又搀他到木椅上,两个人都朝着门外的雨听电波传来的歌声。 “三月里的小雨” “淅沥沥沥沥沥沥沥沥沥下个不停” 小孙惬意地闭上了眼睛,感觉湿润的空气轻吹着脸,虽是小雨但也是密的,挤满了今夜这无人说话的空气。 “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 “带着我满怀的凄清” 他偷偷看阿仙,阿仙是微笑的,她甚至无声地唱着,“我想她是喜欢唱歌的,”小孙想,“可惜了。” “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说” “可知我满怀的寂寞。” 阿仙和小孙都背负着自己的过去,看了半宿的雨,听了半宿的歌。 小孙最后在椅子上睡着了,卷着雨声。第二天醒来,发现有人给自己盖了一条薄被。 那天早上吃的是葱炒鸡蛋花,黄灿灿的鸡蛋盛在白瓷盘里,很赏心悦目,小孙很喜欢。 “你很喜欢鸡蛋花吗?”阿仙注意到了。” “你不觉得鸡蛋的颜色和水仙一样吗?”小孙写道“在我能看见的时候我就这么觉得。” “能看见的时候?” 小孙把他的人生分为两部分,带墨镜前带墨镜后。 “是啊,我原来也是看得见的……”他写道,可是要写什么呢,写他目睹了家庭的破裂,写盲眼的师傅教给他为人处世的道理? “当你带上墨镜的时候就是个盲人了,不管怎么样,你已经踏进盲人的世界里来了。” “这比重新去适应正常人的人生更轻松。” 阿仙没有问下去,就像她也不肯讲自己不说话的原因。 夏天在水仙枯萎后就来了。 小孙的生日快到了,阿仙问小孙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小孙说,我想知道你什么样子。 阿仙笑着写道。 “我知道了!” 晚上的时候阿仙支起了小桌子,放上一个小蛋糕,还放了两碗鸡蛋面,阿仙柔软的手打开他的手心。 阿仙照着镜子用纸和盲文描了一张自己的脸。 这是她能想到的唯一让小孙看见她样子的方法,只是她不知道小孙早就把她的每个样子都记在了心里。 小孙摸着陪伴他这么多年的盲文,摸着熟悉的凸点组成一张脸,他在心里许愿。 “我想和阿仙一辈子。” 久违地开了哪家邻里用来抵账的酒,醉了酒,他像是被盛夏蛰了脸,烧起来一颊的红色。 阿仙扶着他去屋里,他躺在床上,用手拉住了阿仙。 “阿仙”他喃喃道,“阿仙” 他从心房位置的口袋掏出那张盲文照片,仔细的摸了一遍,又伸手去摸阿仙的脸,摸过时常蹙起的眉毛和微微珉起的嘴唇,经过鼻子的时候发现她在急促的喘息。 “一模一样。”小孙说。 但阿仙颤抖着,一时间忘记低着头,伸着脖子从小孙的宽厚温暖的手里挣脱了。 与此同时,那双本来看不见东西的眼睛,却在朦胧里发现了阿仙的秘密。 她含着下巴,微低着头遮起的小小喉结。 第二天两个人都没开口说晚上的事,阿仙突然写纸条询问他可不可以为他按一次。 “太瘦了。”小孙心想,阿仙瘦瘦的肩胛骨不像他本人那么柔和,高扬着,像一对骨头翅膀。小孙看着阿仙沉默地趴在红色的按摩床上,突然萌生了一种想紧紧抱着他的冲动 因为很害怕他就这样飞走了。 “男人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他心想,“我就是喜欢他。” 他愿意一辈子盲着,守着阿仙的秘密。 阿仙走的那天没有任何征兆,也就是那一天,小孙真的老了,变成了老孙。 阿仙就像她的名字,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离开去了哪里,像夜里开放的昙花,没为着任何人开放,也没为任何人凋谢。 小孙喜欢她的决绝,也恨她的决绝,她是喂不熟的猫,是死活不肯开花的年的水仙。 他恨她花蕊一样的睫毛抛洒芬芳,恨她花瓣一样的嘴唇不肯说话,他是个卑劣的健康人,用假装的残疾获得了短暂的幸福。 他想起师傅说的那句话 “不管怎么样,你已经踏进盲人的世界里来了。” 来年是年了,大学生的收音机很快被淘汰了,老孙低价收购了收音机,却没有买下磁带——因为他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包裹,里面是一盒自录磁带。 是一个男声唱的《三月的小雨》,从此老孙一边听这首歌一边吃葱炒鸡蛋花一边想阿仙,想阿仙为什么男扮女装,想他原来也在假装不会说话,想他,喜不喜欢自己。 不过他一个答案都不知道,回答他的只有那盒被反反复复听的磁带。 “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说” “可知我满怀的寂寞。” 不过要说是否有什么其他变化,就是隔壁花店莫名失掉了一个买水仙的大主顾。 隔壁的盲人按摩店门口依旧是绿绿葱葱的,是一盆盆大葱。 若是问他为什么养葱。 他一定告诉你,大葱不开花。 幕后故事 小孙的过去 阿仙的过去 标题的由来 小孙的师傅是一个假盲人,后来被拆穿后所有人都后怕,因为人在盲人面前是很松懈的,会泄露很多秘密。 临死前师傅告诉小孙,既然已经选择做一个盲人,就不能回到正常人的世界了。 阿仙小时候被xq过,家里人觉得男孩子发生这事很丢人,连带着觉得他不正常。 于是阿仙想“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子大家是不是就不觉得奇怪了”,所以为了掩盖真实性别他宁愿不开口说话。 他们两个的人生都浑浑噩噩没有范本可以参照 所以叫:六神无主 可在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danhuaa.com/jdhxx/8761.html
- 上一篇文章: 那些花儿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