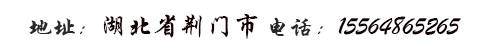参赛作品选发吃天光
|
在哪儿治疗白癜风好 https://m-mip.39.net/nk/mipso_6983142.html 吃天光 西安美术学院谢清如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群体能够拥有完全一致的共同爱好,更别提将其长期保持了。可是从情感的角度分析,有一项活动的魅力连最挑剔的人也无法抗拒,那就是“食”。自然,我也如芸芸众生一般,是“食”文化的拥趸。 我素来爱演讲,又爱美食,说起吃来眉眼都比往常鲜活三分。偏生又挑嘴,吃不胖,于是小小年纪练就了一番挑剔毒舌的胃口。每到深夜来临,我就坏心地和同寝的室友细细描绘家乡菜的做法,从皮到汁,能让人口舌生津。米面的鲜香,鳜鱼的辣香,小龙虾的麻香,烧饼的脆香,冬笋的清香,茶叶的苦香,我能说出一朵花来。说得自己一个劲儿咽口水,馋得朋友们一个个眼冒绿光。我的家乡在长江下游的徽州,那个曾被夸赞为“天上新安”的人间之境。这里诞生过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的徽文化,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曾经独占商业界鳌头四百年的徽商。这里是东南邹鲁,朱子故乡,是有着“中国语言活化石”之称的徽地。南腔北调都在这里聚集,文化的积淀让徽州人重传承、诵诗书、敬礼节,以至于发明了很多文绉绉的吃法和菜名。晨起用什么,夜深后尝的是什么,徽州的百姓分得那就一个清楚啊! 就拿一日三餐来说事儿吧。早饭,徽州人叫“吃天光”,午饭是“吃当昼”、“吃当头”,晚饭则是“吃落昏”“吃乌昏”,还有夜宵,那又是“吃夜深”了。日子久了,老人只说得清这是古时候流传下来的话。有多久呢?说不定是尧舜耕种的时代吧。先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碗里盛着日出日落,朝霞与夕阳。那是田园牧歌的朴实,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浪漫。徽州的早晨吃的是一天的开端,一年的盛景,带着南方人吟诗颂雅的清俊和风趣。在我的记忆里,从小学到中学,清晨挤在校门口的小吃摊永远是一成不变的。零几年的时候,五角钱便能买到刚出炉夹着火腿肠的雪白大馒头;铁锅里的油糍煎得两面焦黄,咬一口就露出热腾腾的米馅;火炉怀里煨好的烤饼有两种馅儿,甜的如蜜糖,咸的像含着干火腿;街角的鸡腿个大皮脆,上面悉悉索索撒了好些白芝麻和胡椒粉;马路对面的馆子一碗六元的面卖了十几年,面条里的雪菜笋片却还一如既往的好吃。正在抽条的少年少女们嗷嗷叫着扑上去,饿狼一样狠狠地吃,匆匆几口下肚就又当起翩翩学子来,彼此之间低声交谈着,眼神交汇中还转着点小心思。但若是真跟对方对上眼了,就赶紧低下头大咬一口鸡蛋煎饼,然后被鲜红的辣椒丝惊地嘶嘶吸气,从额头到脚尖,连白净的面皮都烧得通红。青春的身体若没有一副好胃口,估计是做不完那么多功课的。南方的空气湿润又黏重,可每到这种时候,便是连空气里都掺杂着食物的烟火人情味儿了。 我就比较幸运了,不用那么狼狈地赶早。若是去吃学校门口的摊子,得六点半起床,还没有家里的讲究。于是疼爱我又手巧的母亲就亲手为我做“天光”了。在我家里,主厨的掌勺向来是外婆与父亲把控的,但论起甜点小食,没有人的手艺能与母亲相提并论。阳光迈过窗檐的时候,母亲就把鸡蛋土豆饼就煎好了。一股葱香混合鸡蛋、土豆泥的香气爆炸出来,刺激得我朦胧的睡眼一下子就清醒过来。这时候我就冲到厨房里,将小锅里的饼舀入盘中。饼是诱人的金黄,上面星星点点散落碧色小葱,暗红的辣椒粉,薄脆的边缘还拉着丝。咀嚼的时候几层丰富的口感层迭在一起凶猛地撞过来,鸡蛋混合面粉与土豆泥的香味轰炸着味蕾,薄的部分酥脆香辣,厚实的部分油香劲韧,好吃得舌头都能一口吞掉。我有几次偷偷带到课堂上吃,于是全班同学只能一边魂不守舍地念书一边闻着香气咽口水。但自从念了大学,远离了那江南水乡,便只有寒暑假才能享这等口福了。 如果说鸡蛋土豆饼的味道是炽热燃情的,甜酒年糕的味道就是细水长流的,痴恋而缠绵,仿佛酝酿了一千年的深情。不声不响又极度温柔懒倦地依偎过来,就像打碎了一只陈年酒坛,酒精在夕阳下蒸发,只余空气中的一点甜味。甜酒,在徽州也唤作酒酿,酒糟。做甜酒是每家每户的女人必备的技能,过年前就要备齐材料。一只皂色的酒瓮里盛满了洁白的糯米,外头裹上厚实的棉被,放在温暖的火桶里等酵母发酵,就像盼新生儿一样盼望着,终于,酵母温柔地浮上来,米酒散发出甘甜的酒香,“甜酒”就大功告成了。低头轻抿一口,不由得让人感叹:“还是自家酿的酒最清甜!”这样的好手艺,母亲教给女儿,女儿嫁了人又教给新的女儿,就这样一代代传下去,就像新安江的水波一样,渊远流长,昼夜不息,奔流到底。 以前那江南水乡的古道边,酒馆饭馆的马头墙下总会站着一口大缸,缸里盛得是比蜜还甜的酒。清晨穿红着绿的小妇人俏生生立在墙下,看见撑着小船要去跑码头的十三四岁少年郎,就用柔柔的嗓音唤他们“谁家的小官?吃完酒再走!吃烧酒还是甜酒?”船上的少年就会涨红了脸扯着嗓子喊:“小伢才要得甜酒!我是个大人啦!”但最终还是败在女子弯弯的笑眼里,竹篙将船一撑就跳下来。接过满得差点溢出来的甜酒,那甜酒里必还卧了两个甜水鸡蛋。在甜酒里打上鸡蛋,是最古早的吃法。鸡蛋的滑腻水润和甜酒的绵长沉郁撞在一起,就是一个能够醉死人的拥抱。 武汉人在夏天的傍晚喝甜酒,是为了避暑气,徽州人在冬天的清晨吃甜酒,是为了去寒凉,滚烫的一碗酒吃下去,从头到脚整个身子都舒展了。给过完年就要去跑码头的孩子吃一碗,再多往碗里打个鸡蛋,临走时给他带上三条绳。行囊坏了可以用那绳系上,走投无路时便用那绳上吊,“出门身带三根绳,万事不求人。”徽州人多地少,多丘陵山地,只靠耕种是无法养家糊口的。“前世不修今世修,苏杭不生生徽州。”,多少人泪别父母妻子,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期望投身商海。“十三四岁少年时,告别亲人跑码头。”,谈起徽州,都会说徽商是天下第一大商,徽州人精明肯干,徽州十八里乡繁华若锦,又有谁能知道少年郎背后的心酸和思乡情?临行的时候喝一碗家乡的甜酒,饮尽最后一点温柔,未长成的雏鸟就扑向了那狂风海浪。 “徽州徽州梦徽州,多少牵挂在心头,句句乡音阵阵愁。”在外的游子在西风黄沙里怀念的是家乡的白墙青瓦古道口,新安江水万古愁,江南折过的花,江北饮过的马。风霜雨雪里贪恋着母亲温暖的手,仿佛还是清晨缩在自家的被窝里,母亲掀起被子,轻轻地唤:“吃天光喽!”然后含泪笑着在梦里醒来。“前世不修来世修,来世还要生徽州。”不管世界有多宽大,在外的旅人心心念念的永远是那片山水和活在山水中的人,和一句乡音,一声“你家来啦”。第一场雪一落,就到了游子归家的时候。出去时身无长物,过年时衣锦还乡也罢,两手空空也罢,都该回家了。大年初一在鞭炮隆隆里醒来,入手便是母亲递来的盛满甜酒的碗,甜酒里滚着自家做的年糕和小圆子,年糕片得很薄,圆子掺了桂花的香气,碗里散落几枚鸽血红的枸杞,一碗灌下去,滚滚热气就从胸膛爬遍了全身。新年的第一顿天光,不仅是许愿岁月和美、新年新貌,同时还是平凡人家对一家人能够身体康健、天长地久的一点念想。 过完年,游子再次归家,便要等到清明。说起来,今年身在异乡,无法回去同父母一起踏青,扫墓,喝春酒,是我的不是。往年这时节,满街除了黄白菊花、艾蒲卖得较多,就属清明馃最惹人喜爱。馃,同“果”,是徽州对饼一类的食物的传统叫法,清明时节,吃天光势必要吃清明馃。在我居住的小区,有一位阿婆专卖清明馃,清明前后她必定准时出现在马路边,支起她的小铁锅开始干活。她做的馃,厚实,块大,微微有些粗糙的饼皮是碧绿的,揉进了艾草的清香,嗷呜一大口,就咬到肉香四溢的馅儿。那肉肥瘦适宜,被反复捶打成糜,混合肉丁和小块的软骨,夹上嫩笋片、雪菜丝、马齿觅,里面渗出来的油都是橙黄的,咬一口唇齿留香,只余一声满足的叹息。清明的时候啊,徽州的油菜花都一大片一大片地开了,金灿灿的一汪海洋在山坡上流淌。映山红也漫山遍野地烂漫,艳丽如血,恍惚间仿佛比天际的晚霞还叫人沉醉。青石板路遮掩在花叶下,顺着凹凸不平的石板走过去,远处依稀能望见祭祖的祠堂,白墙青瓦,屋檐边缘滚动沉默的金光。游客们只会感叹祠堂的恢弘高大,徽派建筑的构建精巧,殊不知这祠堂的一砖一瓦,都是先辈对子孙后代的不舍与期许。多少徽商身无长物时出门闯荡,随身的包袱里始终装着一本书和一双母亲亲手纳的布鞋,除了长辈渴望子孙后代向学的心愿外,还有自身对学问的追求与向往。因此徽商若是衣锦还乡,必会在家乡修建祠堂与学堂,以祈愿学风昌盛,雅言盛行,九泉之下的先祖也能安息了。因此,清明时节,整个徽州都是这样的景象:冥蒙薄雨,烟波衡翠,学堂书声,祠堂青烟,牌位前供着一碟清明馃,一篮菊花,一壶酒,也许还有一枝打了水花的映山红。 在外念书学习,一个人的时候偶尔会想,我曾走过天涯海角,见过多少名山大川的风光绝伦,最牵挂的却始终是青山环抱的那一方江南水乡。我的左手边是北方的大漠孤烟,右手边是南方的亭台楼阁,心里却住着村头的古树,堂上的飞燕。我虽对无数佳肴珍馐评头论足,但偏好的还是家乡的粗茶淡饭,晨起饮天光,当昼食秣粮,落昏月夜深。曾经在多少个午夜梦回,我想温一碗甜酒,就着水波中的月光。但终究是轻轻地吐出一口长气,仿佛下一秒就能听到一个声音念道“我的身前是殊途,身后是故乡。” 文学万里行感谢您对大学生文学事业的支持!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danhuaa.com/jdhwh/5691.html
- 上一篇文章: 我的童年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