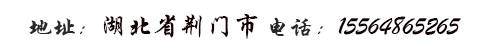诗集下周见欢迎文后扫码预定修改版,
|
北京哪家白癜风医院最好 http://m.39.net/pf/bdfyy/xwdt/ 我喜欢你一如这旷野般色彩明丽(代后记) 郑书慧 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上诗歌呢?不知道,就像问我什么时候爱上你的一样,不知道。我想,很多时候,爱的发生,最初都来源于孤独和恐惧吧。 小时候,我是个胆小内向的人,敏感又羞涩。害怕跟陌生的事物和陌生的人打交道。放学路上总是低着头溜着墙根走,怕碰见熟人(当然是大人)要打招呼;家里来了客人,我就会躲进里屋不出来,因为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爸爸教我:“你不会说‘吃了吗’?”我振振有词地反驳“明知道人家吃过了还问,不是虚伪吗?再说人家要说没吃,那接下来不是要留人家吃饭吗?”还怕被妈妈指派出去借东西(小时候物资短缺,家里很多生活必备品都是缺东少西的),比如要到大妈家借个筛面的箩,到二婶家借个量米的升之类,甚至一勺盐,一碟醋。这是最让我头大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开口,开了口也不知道怎么说啊。 (一岁半看我胆怯的小眼神) 最怕的就是放学回家被困在门外,等待让我倍感不安。那时家里的大门还是一扇木栅栏拴着一把长长的链子锁。每次快走到家的时候,我就会走一步在心里念叨“有人”,走一步在心里念叨“没人”,心情高一下低一下,玩“点兵点将”一样一直数到家。大门开着就一阵狂喜,可更多的时候看到的都是那把冰冷的链子锁,于是只有靠在门上对着大路张望。往往都是快天黑的时候,父母才下班回来。其间最难熬的就是要经受一个个过路人的目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不知他们的目光里都包含什么,总之都让我害怕和尴尬。 (三岁至三岁半和妹妹还是胆怯的眼神) 还有两个经历让我对被丢失特别恐惧。记得有次坐公共汽车,大概是四五岁时吧,不知为什么,妈妈和售票员吵起来,售票员把我妈推下车,而把我留在车上不让下(印象里的售票员、售货员大都凶神恶煞一样,不敢得罪的),最后一直把我拉到总站。我坐在冰凉的长椅上一直哭一直哭,到了很晚妈妈才找到我把我领回去。还有一次跟爸爸去火车站看电影。我家跟火车站一墙之隔,那墙还被附近的村民掏个洞,方便来往。从铁道上翻过去再从检票口穿过去,无论是去公园还是去市里都是很省力省时的事。而火车站也成了附近小孩子们的玩耍天地。穿火车道成了每个小孩的必备技能:小的笨的从车厢下面弯腰钻过去,大的麻利的从两车厢连接处的大铁链上翻过去。白天在检票口的绿色扶手玩“抓人”,晚上拿着葡萄糖输液瓶去站台上逮蛐蛐,回来油炸吃。那时火车站的大院里经常放电影,有时没有屏幕,就在白墙上放映。那天看完电影《地道战》还是《地雷战》记不清了,我们翻铁道回家。跟着爸爸自然是不用弯腰钻火车的,因为钻的风险是一不小心会蹭一背的油污。爸爸带我从上面过,先把我抱到车上,他翻过去后再把我抱下来。他的大手刚把我放到两节车厢连节处的大铁链上,一不留神,火车就开了。我吓得大哭,爸爸喊着我的名字追,声音都变了。他跑了十几步,把我从火车上抢下来。这两件事都给我的心里造成很大阴影,特别怕被整丢,怕一个人被丢到陌生的境地。那种茫然无助的恐惧感长时期都在梦里延伸着。 (八岁多吧,第一次骑到小三轮,还是人家的) 还有就是家里遭贼的经历,一次应该是还未上学前,那时还跟爸妈睡一个床(这个记忆让我奇怪,我只比我妹妹大两岁半,那时她睡哪里?莫非是我三岁前的记忆?)半夜里妈妈照着手电筒打蚊子,突然看到一个小偷蹲在窗户下,然后尖了声地叫“进贼了——”,然后我爸就冲出去抓贼。最终是没撵到。一次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下午放学回家,见大门敞开着,院里很奇怪地站满了人。一进屋,还看见两个穿着公安制服的人,我妈坐在地上大哭,几个女人围着劝慰。原来,家里又进贼了。柜子抽屉床都被翻遍了。那时也没啥值钱的,好像丢的最值钱的是几卷粮票,尤其是贵重的全国粮票。也许是我家住在路边的原因,贼频频光顾,半夜里鸡窝被摸光了,洗完还没晒干的衣服被卷走了,等等。总之,家里遭一次贼,我的恐惧就多一分。记得我成年后还做过一个被贼惊醒的梦:我正在睡觉,突然睁眼看到童年院里的大槐树,每个树杈上都蹲着一个小偷,还抽着烟。黑暗中红光一闪一闪地,在对着我阴阴地笑。 孤独和恐惧让我变得更加敏感,也让我的小脑瓜充满想象。我常常在一个人的时候,看着破墙上纵横的裂缝,把它想象成各种图案;比较天上哪朵云更像狮子,那匹马比哪匹骆驼更漂亮;后来喜欢站在树下,仰头从树缝里看天空,看太阳、看月亮,看云。变换不同的角度和距离,熟悉的事物呈现出新奇的形象。也许就是那一刻,我发现了一种审美吧。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都还有。不过现在更多地是单纯地看树。南方的树种多,树的形状也多。一个人散步的时候,就会给各种树打分,最后评判的结果是:喜欢木棉、异木棉、凤凰木、鸡蛋花(鸡蛋花虽然名字很俗气,但它的枝和叶和花都很有质感,各有各的看头),最不喜欢的竟然是紫荆花,枝和叶都凌乱的耷拉着,花也是皱巴的,整棵树给人的感觉是蓬头垢面、垂头丧气的样子,只有一场风雨把花都吹落到地上,它才突然现出一种惊心动魄的美,那种凄艳和哀伤让你忽然对死亡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就是这样地爱上美的吧。放学回家,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狂热地去画觉得美的东西,画着金鱼的脸盆,印着郁金香的挂历甚至妈妈结婚陪嫁的红被子上绣的凤凰,都成了我仿照的对象。从此有玩伴时就一起玩,没有玩伴时就画画,靠近美、感知美、迷恋美让我愉悦和兴奋,让我忘却了孤独和恐惧。 (十七岁高中毕业的暑假) 到了高中,开始不可救药地迷上武侠。带我上贼船的是和我同龄又是小学、初中同班同学的小堂叔“小友”。小时候他就是我的最佳玩伴,打四角,滚铁环,打溜溜球,爬树掏鸟窝甚至女生玩的跳绳跳皮筋他都无一不精通。往往是我帮他在桌上补习功课,他带我在地上过关斩将。我们一直很好的感情,我从来不叫他叔,一般叫他“小友”,当他和别的男孩子一起往我辫子里扔苍耳籽的时候就骂他“郑清友,你个死清友!”后来他真的死了,在三十多正盛年的时候,喝完酒摔死在雪地里。我曾在Q空间里放过一篇文字《忆小友》来搁置我的哀思。上了高中就不多来往了,但有一次看他拿本书看得津津有味,便要过来看,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武侠小说。当时都不知道书名是什么,但记得主人公叫“段誉”,他掉进了一个洞里,发现一个美丽女人的石像,得到了一本武功秘笈,学会了什么神功和凌波微步,从此厉害得不得了。还记得他看到女人体时的砰砰心跳的描写也让我怦怦心跳。后来才知道这本就是金庸大名鼎鼎的《天龙八部》。那是他在火车站附近一家租书店租的,好像是押金十块(相当于我两周的伙食费),一本1角的样子。从此我俩就又凑一起了,他租一本我看一本,为了赶上还的时间,都是一目十行、囫囵吞枣,所以很多书名和人名都混在一起了。就这样,看了金庸、梁羽生、温瑞安、倪匡和古龙。那时最喜欢的就是古龙,古龙笔下最难忘的就是《边城浪子》里的傅红雪了。漆黑的小屋、惨白的手握着漆黑的刀柄,抽刀抽刀再抽刀,一个动作练习十八年,就是为了去报一个血仇。他不懂人情世故,不懂温柔与爱人,只有被仇恨灌满的痛苦和责任。可是到了举刀砍向仇人的那一刻,被告知,这个仇恨跟他无关,他只是个被顶包的孩子。而那个真正被灭门的名门之后是“叶开”,人家已放下仇恨,潇潇洒洒、笑对人生了。我一下子被这个故事抓住被傅红雪抓住了。现在想想也许是先天的母性与受虐心理吧,让我对这种骨子里有着抑郁伤感气质的悲情英雄总有一种迷恋,比如说后来又对《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德烈公爵情有独钟。中年后再读,才觉得《边城浪子》里的叶开和《战争与和平》里的皮埃尔伯爵才是女人的最佳恋爱和婚姻对象。前者让你迷恋和痛苦到都不能自拔。 (傅红雪) (叶开) (安德烈公爵) (皮埃尔伯爵) “孤枕侧畔,一灯如豆,看尽万千红尘旧事;刀枪入梦,剑气漫天,重温多少江湖恩仇”。整个高中我都沉溺在武侠世界里,当时同学对我的印象一定是个不爱说话默默用功的女生,谁知道我在本子上画英雄,在心里恋英雄,在安静的外表下激荡着一颗刀光剑影的心呢?少年心事当拏云。也许内心的英雄情结就是这样形成的吧。我高中时给自己的习作起名为《剑影》,后来给我女儿起的名字叫“莫邪”。“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姿气概是我青春热血的向往,无奈自己只是个柔弱的女子,做不了这样的英雄,只能在雨天的夜里,辗转反侧,等待那“铁马冰河入梦来”。正像泽平看我:“灵魂渴望的是一种轰轰烈烈的江湖纵横驰骋的快意,而肉身却无法跨越生活的鸿沟,只能在尘世的光阴里,饱尝着岁月的留痕。” 大学的女生都在迷恋琼瑶,而我却拒绝琼瑶迷恋三毛。她的随性又执着,淡然又炽热更和我的心意,而心底也暗自渴慕,自己也要有个爱得昏天黑地的“荷西”来走遍撒哈拉。再后来,真的发生了一场昏天黑地的恋爱,却连小小的平顶山都没走出。短暂而锥心。 (十八岁的向往) (十九岁的初恋季节) (二十四岁的憧憬) (三十四岁为人母的幸福) 其实谁的人生不是充满失意和无奈?爱而不得的痛苦,得而患失的焦虑,为名为利为情,概莫能逃,越积越深。也正因为这份无奈,才会有不断的挣扎和不断的努力,人生才会饱满而鲜活吧。但也正因为此,人,就更需要为自己的焦灼和痛苦寻找一个出口。犹记得四十岁那年,有天照镜子时发现脸色发黄憔悴,瞬间明白了“黄脸婆”的含义,原来它并不只是一个揶揄的说辞啊。四十三岁那年开始长白头发,四十四岁那年眼花了——衰老,正一步一个脚印地逼过来了。胆囊息肉,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这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病灶是岁月给我的温柔一刀。挨刀子的确让人烦恼,但又觉得隔个三年五载的小手术让我的身体就像是大战前的演习,熟悉敌情,获得经验,真正大敌当前的时候就会临阵不乱甚或者日常加强了备战就不会有大敌来犯了。所以我并不是很怕身体的疾病和衰老,我更怕的是精神的抑郁和麻木。 充满老妈子式的唠叨和抱怨;充满对年轻人的嫉妒和不屑;充满对男人的嫌恶和排斥;充满对工作的懈怠和厌倦,对新鲜事物不再感兴趣;对自身形象不再做要求;“都到这把年纪了,还想啥呢”……这一切,才是女人衰老的最大推手,心先老了,身子跟着就老得快了。 (44岁的自拍鬼脸) (五十岁的影棚写真) 我的抗抑郁抗衰老的法宝是“买新衣”,“拍美照”,“养花草”。现在女人最常说的“包治百病”,买一个包包的治愈功能是多么强大。我不怎么喜欢包包,但喜欢买衣服。买到一件合身称意的衣服,看它包裹着还算纤细的腰身,在镜子前来一番左顾右盼,那种美滋滋是大老爷们难以理喻的;在花下拍美美的照片,闪光灯的遮瑕功能把自己变成白雪皇后,合适的角度美化了松弛的皮肤,虚化了眼角的鱼尾纹,哎呀,原来我还这么年轻啊。自欺欺人地陶醉一番,忘了自己是中年大妈了;拿着剪刀在几十盆红红绿绿的花前左一刀,又一刀,剪去枯枝败叶,再撒上几粒花肥,随便一消磨就是一个钟光景,哪还有时间去抱怨去哀叹,去计较鸡毛蒜皮呢? (自家阳台的花) 然后,不知哪天,突然地就爱上了“写诗歌”,也许那根本就算不上诗歌,只能叫分行的句子,但它的确成了我的第四大抗衰法宝。本来天性就爱胡思乱想,加上经常失眠更爱胡思乱想。脑子里突然蹦出个句子,掏出手机记下来,又顺便地想几句,好了!赶紧发到朋友圈里,就像厨师琢磨出了一道新菜式,果农培养出一个新品种急于发布似的,爽。如果再有一帮朋友为你喝彩,那就更爽了。 而且,这个法比前三种更为灵活自由,因为,它是完全由你自己掌控的。高兴的时候,想写几句就写几句;不高兴的时候,想写几句就写几句。好的情绪坏的情绪都得到宣泄了。很多人都说郑老师怎么看着越来越年轻了,哈哈,我只是怀着一颗童心,把童年的孤独寂寞再涂抹一遍;怀着一颗丹心,把少年的狂热激情再温习一遍;怀着一颗爱心,把青春的缠绵浪漫再追求一遍;怀着一颗诗心,把中年的荒芜杂乱再抚慰一遍。幸福的与痛苦的,快乐的与哀伤的,平静的与狂乱的,缺失的与圆满的,都是上天所赐我的,让我生长的福报。不舍得丢不舍得丢啊。 所幸的是,周围的朋友都爱我,呵护我,不管我写的怎样幼稚和凌乱,他们都为我加油。比如说我高中的语文老师傅春杰老师,都七十多岁了,还总是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danhuaa.com/jdhhy/5912.html
- 上一篇文章: 安纳塔拉新春特惠1K抢西双版纳l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