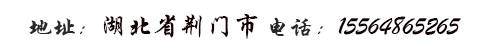张晓红海鲜羹里的旧日味道
|
海鲜羹里的旧日味道 文︱张晓红海鲜,是我们家乡宁波人的心头之好。宁波人是靠海吃海,已形成了丰富的海鲜文化。老话说:无海鲜不成席。就是闲常人家过寻常小日子,也是把鲜忽忽、咸勒勒的海鲜“下饭”(菜肴),吃得活色生香,有滋有味。 家乡的海鲜,分大鲜和小鲜。大鲜,指从深海里捕获的鱼、蟹、虾。小鲜,是从近海泥涂上抲来的、体积较小、数量多且价廉味鲜的“泥涂货”。比如梅蛤、蛤皮、蛏子、小青蟹、望潮、弹涂鱼、小虾、泥螺等等。 早年间,家乡周边多海滩泥涂。从春季开始,最旺发是夏季和初秋季,正是那些“泥涂货”肉质最壮、最肥厚饱满的时节。 勤劳的下涂人,待东方刚刚显露出一抹淡淡胭脂红之时,就去“赶小海”了,还相跟着几位十三四岁的小孩。这些小孩各自带上一只小田箩,在滩涂的近处,瞄着一个个由脚印踩踏而来的小水潭,小心前行。在这些小水潭下面,总有那些“偷懒”的青蟹,大多是小青蟹,以此蛰居为家。小孩们把脚板踏上去,它们就动弹不了了,只能束手就擒。 大人们以木质海马为滑行工具。蹬着海马抲望潮、钩蛏子、撮泥螺、撬牡蛎……在泥涂里,一粒粒捡回来;在小洞岩壁上,一撮撮挖出来;在泥沙深层中,一颗颗掐出来。 木质海马,简称木马,也称泥鳗船。这是一种小巧玲珑、能在滩涂上轻快滑行、行走如飞的船形工具,相传是民族英雄戚继光发明的。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屡次登陆扰乱我沿海一带,朝廷派戚继光来浙东抗击倭寇。无奈,当时滩涂泽乡为主的家乡,迈不开马蹄,等戚家军追到潮头,倭寇已登上贼船,逃之夭夭。 戚将军偶看到滩涂上的泥鳗,摇头摆尾,畅行流动,他灵机一动,叫人砍了毛竹,做成翘头宽尾的泥鳗状竹船,一试,果然其行如飞。戚将军率领将士驾泥鳗船训练,如虎添翼,终把猖獗的倭寇从海上赶跑,打了几个大胜仗。 戚家军用泥鳗船抗倭的佳话越传越神,泥鳗船也成了人们下海涂劳作的工具。 每逢农历的月初和十五、十六的“大水头”,家乡古桥的集市上,就有下涂人的摊子在卖刚从泥涂上抲来的小海鲜,种类丰富,价钱公道,近于贱卖。用大毛笋叶或荷叶包着一包包梅蛤、哈皮、蛏子等,足有半斤多,只需五六分钱。 这些小鲜,我们小孩也最好这一口。中午饭吃了后,跑出去玩儿,邻家大人问:中午吃啥下饭?小孩扬着头,神气地说:吃的小鲜羹!鲜得来,头发会脱落! 这些小鲜,都喜欢烧成羹。古人说:“羹者,五味调和者也。”羹,是家乡人素来喜爱的一种菜式。餐桌上如没有一碗羹,会拄着筷子,米饭难以下咽入肚腹。这羹又不同于“勾芡”。勾芡是把荤的主料沾一下芡粉,在锅里爆炒,属炸炒类菜肴。如居家筵席,无论多高档,上的热菜,也以一碗碗“热羹”居多。羹糊,宛如水晶珍珠粉,把荤素食材放一起,搅糊,众和,烧熟,就成了色香味俱全的上好菜肴。 烧小鲜羹,羹粉很有讲究,定要在自家的小石磨上磨一碗早稻米粉。早稻米粉,有自然的稻米清香,涨式好,有骨姿,回味悠长。调和众味皆出鲜,也能保持鲜中的维生素营养不至流失,又能使羹的数量随需用而大增。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家吃饭人有六七个,当家女人往往是一锅饭,一锅羹,一起烧,饭熟羹好,照样能让每个小毛孩一人一碗色艳透鲜的小鲜羹,呼啦呼啦地吃得欢。那是恣意舒畅地吃,吃得满足、自愿放下筷子的吃。 花五六分钱买来小鲜,再从自家菜园掐来些茄子、夜开花、小白菜,就可烧出一锅羹。那时吃油凭票供应,一人一月一两半,放油称为滴油,做小鲜羹就可不用滴油,也不用弹“味之素”。那时味精叫“味之素”,用时为弹,弹出一二三粒即可。味之素用拇指大些的腰鼓状的玻璃瓶装,黑色电木旋钮盖上,雕有一朵佛手花。这是上海味精厂最早生产的“佛手牌”味精。在乡间,也只有“上海工人”的家属才有那稀罕珍贵之物,但在小鲜羹里也可免了。 那时我家住在农村,父亲是上海工人,生活较之村里的农家要好些。大清早,母亲要去街市上买菜,买我们喜欢的小鲜,尤是小青蟹。我就倚在门外。稻田环伺的小村庄,清禾绿苗,田水盈盈;蝴蝶蜻蜓,翩跹飞舞;又有蛙鸣蝉噪,沟渠水淙淙。清晨的薄雾,萦绕在田野,如纱如幻。那水声,那翠色,那蝶影,就从飘飘渺渺的雾纱中隐现。 母亲就是从这条美如仙景般的田间小路上回来,穿着淡紫红白色细碎花的衬衣。青菜小葱、豆腐、小虾,蹦跳的弹涂鱼、噗噗吹气泡的小青蟹,满满一竹篮。母亲衣裳内敛的红,和竹篮里的绿色、白色、乌青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竹篮的丰富,和远处近处飘漾的原野上清凉的芬芳,富足,香甜。 这一竹篮,足以吃三四天,今天必先吃小青蟹,我和弟弟就来到灶间看热闹。 母亲已在灶前灶后忙碌,脸上闪着晶莹的汗珠。灶台的砧板上,已放着一把洗净了的梗白叶翠的小白菜。那是夏季才有的绿叶菜,很难种,很难伺候。下籽落土后,只能在半夜无天光时勤浇水,才能出芽成活,娇贵得很。清香有涩味,夏天吃了能清凉败火。这种正宗的小白菜,现已绝迹。我们家做小鲜羹,就喜欢小白菜。 邻家几个调皮小毛孩,探头探脑张一下就跑出去,在外面高声地嚷着:小白菜,嫩爱爱,老公出门在上海,雪白洋钿带进来……我和弟弟听了不高兴。母亲笑着说:这是小孩们说着玩的,由他们说吧。 砧板上还放着两串张牙舞爪、噗噗吃气泡的小青蟹。一串五六只,七八分钱一串。都比铜钱稍微大一些,最上面一只有鸡蛋般大。用蔺草绳紧紧扎住,但都威风凛凛,霸气不逊于大家伙。曾有古诗形容: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足见蟹的“霸名”之威。 我和弟弟最喜欢母亲买小青蟹,原因之一,就是能把它的“横行不法”一下子除掉。母亲将一只毛竹筷按在小青蟹的肚脐上,我们拿来菜刀,用力在筷头上“叮”地敲一下,它马上就威风顿失,难以动弹。我们很有些得意。 母亲把小青蟹对切成块,切口处用米粉封住,免得金黄浓稠的蟹黄流出来。把小青蟹块下锅烧熟,然后放切成寸段的小白菜,再马上放用水调匀了的米糊,配以适量的水,锅铲轻轻搅翻几下,就可起锅装碗。 看母亲拿锅铲的手,如同她拈针线般的轻柔。小白菜嫩,嫩得不能多翻动;也要防着蟹黄从蟹块里溢出来。 绿白相间翠玉莹莹般的小白菜,镶以红艳艳的小青蟹块,蟹块盖红得浓烈,带着火红金红色,在乳白色的羹糊里隐隐约约,红绿白分明,光是那悦目的色彩,已让人醉了。味道呢,小白菜脆爽略带涩味的清香,小青蟹的肥腴鲜嫩,羹糊的滑溜水润,组合成了来自海洋和泥土的原汁原味的好味道。 还有常常烧的蛏子羹。蛏子,又称“西施舌”,足见人们对它的钟爱和它的美妙。把蛏子洗净,用淡盐水泡上几个小时,让泥吐尽。在沸水中焯熟,剥去两片薄薄的壳,待用。将水灵灵的绿豆芽入锅再入羹糊,待沸,再将蛏子肉入锅一起翻熟,撒一把嫩韭叶,就可起锅。绿豆芽玉色水嫩,缀着圆鼓鼓洁白的蛏子肉。蛏子肉恰到火候,不缩水,不过火,鲜、嫩、肥,好吃得不像话。 也常烧蛤皮羹,白润润又呈青玉色的夜开花刨丝,饰以十几只开壳蛤皮。蛤皮洗净后连壳一起入锅。这是正宗的时下已不多见的“野生蛤皮”。蛤皮壳瓷质硬挺,有黑灰色横式花纹。这一锅羹,火候宜适中。夜开花丝烧至软糯,蛤皮以刚开壳、不老不嫩正好。两片轻阖启口的蛤皮壳,衬托掩映着一蕊嫩黄娇娇的蛤皮肉,好像扯开帆的小船载着花束,在羹糊里泛舟,真不忍下箸,惟恐破坏了这幅美丽图画。 梅蛤烧羹家乡人称之为“梅蛤浆”。梅蛤又称“海瓜子”,因其形状大小如南瓜子,白里透红的外壳,宛如美人耳垂上的玉坠。它还有个浪漫别致的名字叫“虹彩明樱蛤”。古诗《咏海瓜子》云:“冰盘推出碎玻璃,半杂青葱半带泥。莫笑老婆牙齿轮,梅花片片磕瓠犀。”海瓜子是贝壳族中的千金小姐,江南梅雨季节为旺发。肉质细嫩,味鲜美。然而个小肉少,吃起来如嗑瓜子,是绝好下酒菜。于我们小孩子并不合宜。小孩嫌麻烦,把一勺羹舀来,连壳一起嚼,吐弃之,被大人呵斥为“暴殄天物”,就不常烧。除非来客了,待客。梅蛤浆委实是一碗色香味俱佳的上乘之肴。红粉粉的犹如梅花片片的梅蛤,幽蛰在水润柔柔的米糊中,少许切得极细的嫩香“鞭笋丝”,间夹绿莹莹的韭花,可人,犹怜,让人又爱又心疼,不忍吃。 泥螺茄丝羹也是不常做的。泥螺称“吐铁”。清时医师吴仪洛著《本草从新》曰:“吐铁补肝肾,益精髓,明耳目,性甘酸,咸寒。”“桃花开时佳,桂花开时也佳”,吐铁最旺,应在初春或初秋。家乡人喜腌食之。腌制时,颜色乌青。也有直接鲜吃,下锅放水,稍稍一热,吐铁就成了金黄色,味甚是醉人。母亲也常以鲜泥螺茄子一起烧羹。泥螺量不多,但只只有小孩拇指般大,紫莹莹的茄子切粗丝,打一鸡蛋花,撒韭叶。泥螺脆嫩鲜爽,茄丝软糯清甜,吸足了泥螺的鲜,真是好味道。 也偶烧些小杂虾豆腐羹,弹涂鱼、小跳鱼咸菜花羹。这些羹中,都放有切块西红柿,既吊味又增色,我们百吃不厌。有时,羹多烧些,再饭锅里蒸几个“硬米饼”,晚上凉幽幽的小鲜羹就着硬米饼,就是一餐食之难忘的好夜饭。 从小的食谱是一生的养料。如今,我也常常烧各种小鲜羹,虽然食材已大不同,味道不如前,但也足以慰藉那一怀乡愁之情,和缭绕齿颊间的旧日味道。 图片取自网络作者介绍 本名张小红,女,宁波市北仑区人。浙江省作协会员。爱好写作几十年,曾有五、六百万字的作品发表在各级期刊和报刊上。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danhuaa.com/jdhxx/8957.html
- 上一篇文章: 花一些时间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