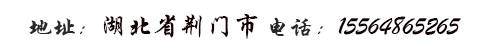黄龙光论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的社会功能
|
摘要: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是西南各族人民千百年来不断适应自然而创制的一系列物质、技术与制度的文化综合体,主要包括水信仰、水技术与水制度等主要内涵。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自然流淌于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文化功能论观察,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发挥着生态系统维系、物质生产促进、宗教精神寄托、民族文化传承与地域社会整合等相关社会功能。在日常具体的水事实践当中,以上几重社会功能同时联动发挥,对作为一个生态共同体的西南少数民族产生一种集生态、社会与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效能。传承、保护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要确保持续发挥水文化的原生功能,这不仅对当前人-水紧张关系的缓和有所启示,而且能为边疆民族团结、生态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借鉴。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社会功能;生态维护;地域社会整合 [作者简介] 黄龙光(诗纳倮乌),男,彝族,云南峨山人,云南师范大学编审,法学(民俗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人类学、艺术民俗学。 [基金项目]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神话研究”(17XMZ) 被称为“亚洲水塔”的中国西南地区,也是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屏障,具有重要的水资源战略地位。西南地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立体气候,自古孕育了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也哺育了西南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小聚居、大杂居的分布格局。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是西南各民族千百年来不断适应自然而创制的一系列涉水的精神、物质与社会的文化综合体,主要包括水信仰、水技术与水制度等文化内涵。[①]功能源于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一种自我满足,文化功能论基于人类社会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学术观察和分析。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经过长时期历史变迁,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一系列社会功能。在水问题频出的当代,为了不断激发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的原生和衍生功能,构建生态和谐社会,首先应该全面总结归纳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的社会功能。 一、生态系统维护自然生人,人化自然,人与自然围绕一系列的人地关系形成一个自然生态共同体。“人与自然的不可分离性表明,人类不是自然共同体的中心,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与大自然具有内在关联的存在。”[②]人与自然的这种内在关联,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也不是一种一对一的平等关系,而是人类自古融于大自然,隶属于大自然。人与自然虽然构成一个生态共同体,但是其实人首先作为“自然之子”而存在,自然是人类的衣食来源,是人类的血缘“父母”。遍布世界各地的所有创世神话都在讲述,水生天地星辰、林木鸟兽、花草虫鱼等世界万物;而所有的人祖神话都在讲述,土地和水是人祖血肉之躯的主要创生原料。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自然可以离开人类而存在,数亿年来自然一直在自我演化和发展,而人类却一刻也离不开自然而独立生活。启蒙以来,人类将自然作为一个客体进行认知和开发,不仅将自身凌驾于本应崇敬的自然,“人定胜天”地大规模开发自然,使人类陷入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淖。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水具有重要的地位。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是西南少数民族千百年来与水互动形成的一套独特的认知理念及其实践机制,其生态系统维护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人-水和谐的生态观与人-水和谐的生态实践两个方面。 作为一种本土生态知识的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是西南少数民族长期适应西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并对水的自然属性及与人类的关系进行全面观察、思考并认知后形成的一套有关水生态观念、知识和技能,这些涉水的生态观、生态知识与技能历经代代相传,不仅围绕一系列治水、用水等水事活动潺潺流淌在代际教习的口耳相承之中,同时被拥有文字能力的那些少数民族写入民族典籍成为经典,这些经典与相关仪式相配合,反过来指导和规约着包括水神祭祀等在内的相关水事实践。傣族谚语说:“大象跟着森林走,气候跟着竹子走,傣家人跟着流水走”“森林是父亲,大地是母亲,动植物是伙伴、兄弟姐妹”,说明从事稻作生计的傣族与森林、竹子、流水之间生成一种亲密关系。傣族人充分认识到森林、竹子等森林植被对水资源的涵养作用,而水资源对从事水田稻作的傣族社会具有命脉的意义,因此,傣族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护林、惜水的生态习俗和规制。 侗族古歌《起源歌》唱到: 姜良姜妹,开亲成夫妻,生下盘古开天,生下马王开地;天上分四方,地下分八角;天上造明月,地下开江河;先造山林,再造人群;先造田地,再造男女……草木共山生,万物从地起。[③] “草木共山生,万物从地起”,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平等共生生态关系的朴素认知。黄冈侗族还有谚“无山就无树,无树就无水,无水不成田,无田不养人”,非常直观地说明了山-树-水-田-人的自然-社会生态逻辑关系,而其源头——山林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体现。 纳西族东巴教认为,人与自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是人与自然生命同源的神圣宗教阐释。东巴经神话《署[④]的来历》讲述人与署的故事,人类与署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人掌管盘田耕种,牧养牲畜,而他的兄弟掌管山林河湖、花草虫鱼与所有野生动物,他们各司其职,和睦相处。后来人类逐渐贪婪起来,进山乱砍滥伐,滥捕鸟兽,污染水源等,结果人与自然两兄弟闹翻了,人类频频受灾,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意识到自己冒犯了署这个兄弟,诚请东巴教祖师东巴世罗请大鹏神鸟前去调解,人与署这个大自然兄弟约法三章,人类必须适量获取自然资源,两兄弟重修旧好,从此睦邻相处[⑤]。彝族先民长期观察自然水的流动性和创生性,认识到水具有源源不断的化育力和生命力,将水认作创生万物的始祖,建构了彝族“缘水而生”的认知论体系,同时,以古老神圣的神话史诗叙事方式代代演述和传承其独特的水生思想。大、小凉山彝族史诗《勒俄特依》(《天地变化史》),叙述天地万物的变化,不仅源于水,而且取决于水的流动和变化。[⑥]在滇南典籍《阿赫希尼摩》中,史诗详细叙述了创世始祖阿赫希尼摩喝下金海水,诞下天地日月、星云雷雨、闪电风雾、山川草木、禽兽稻麦,以及天王地母等各类神祇。人祖则来源于奢祖大海里各色鱼类,经过不断变化成的各色猿变而来[⑦]。流传于云南楚雄姚安、大姚、永仁、牟定等县彝族地区的史诗《梅葛》说:“天上撒下三把雪,落地变成三代人。撒下第一把是第一代,撒下第二把是第二代人,撒下第三把是第三代。”[⑧]彝族“缘水而生”的创世观及其叙事,认为水不仅是天地万物人祖神祇的原生物质,而且因水天然的流动性和化育力,孕育、诞构了天地人神的宇宙世间结构。也正因为天地万物人类都是水这个共同的创世母亲亲生的,所以,人与天地万物是天赋血亲的兄弟姐妹,人与自然之间应是一种平等共生的关系。因此,彝族人-水关系作为一种紧密的亲缘关系,人与水即可天然地避开互相伤害而至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⑨] 生态意识决定生态行为,生态观指导生态实践。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生态系统维护的功能,除了通过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将其蕴涵的生态意识、思想观念与生态知识代际言传外,还有就是通过一系列人-水和谐生态实践的形式实现代际身教。林木植被等天生具有涵养水分的功能,西南少数民族崇拜林木、护林育林的行为比较普遍。傣族全民崇信小乘佛教,笃行“众生平等”的宗教观念。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傣族为了解决炊爨用柴之需,往往在房前屋后种植薪柴林,在采集野生植物食用或药用时,一般只采所需花、叶等,不允许整株拔除,这样就能保证其再生能力。傣族村寨和缅寺的庭院中常种“五树六花”,“五树”指菩提树、大青树、贝叶棕、铁刀木、槟榔或椰子,“六花”指荷花或睡莲、文殊兰或黄姜花、缅桂、鸡蛋花、金凤花或凤凰木、地涌金莲,这些植物不仅是作为宗教仪式植物,也是村寨、寺庙庭院的景观植物。在傣历新年泼水节第二天,傣族举行放生传统。开光仪式后,傣族群众将各自备好的鱼类放入水中,然后必须参加植树活动,意为让树苗和放生的动物一起成长,给那些被放生的动物后代筑巢栖息[⑩]。黄冈侗族有谚“老树护寨,老人管寨”,这种以老树为防护、老人为权威的传统村寨治理观念及其实践,维护着森林生态系统,也协调着人-林(自然)和谐关系。侗族对自然怀有崇敬之心,捕鱼时遵行可持续的原则,织就的渔网有尺寸规约,他们往往“择而捕之,适可而捕”“抓大放小”[11]。 据长期的生活经验,彝族一旦在山箐和密林深处发现有泉源就将其养护起来,周围林木即被认定为水源林而受到保护。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树木就没有水,水必须由树木来涵养。这些树木往往以榕树等杂木为主,四季常青。缺水的彝族村寨,往往还会以民间规约的方式勒石立碑,严禁破坏和砍伐泉源处水源林木。一旦发生破坏和砍伐等违禁的情况,立刻就会有举报,同时寨老们马上召集起来共同商议给予相应处罚。[1]彝族史诗《梅葛》记载,洪水过后柳树因助天神找到人种(葫芦),“天神好喜欢,封赠小柳树,‘小柳树是好树,等到人种找到了,人烟旺起来,倒栽你栽活,顺栽你栽活’。[13]”所以,富有经验的人行走彝区,只要远远看见路边有密集的柳树、柏树等围拢,那儿肯定就有山间甘甜的泉水。路人可一边在树底下歇息乘凉,一边用旁边备好的竹筒舀清凉甘甜的泉水解渴。森林是哈尼族梯田水生态系统的源头,一是涵养水源,一是以林木植被防止梯田被暴雨冲毁。哈尼族认为“树是水的命根,水是梯田的命根,梯田是人的命根”。因此,哈尼人往往将高山森林划为水源林加以保护,把村寨后森林划为寨神林,平日严禁牲口进入放牧,严禁砍伐林木,同时派专门的护林人监督、管护。哈尼孩子一出世,父母就会在寨脚森林里栽下三棵树,将婴儿胎盘埋在树下,用洗婴儿的水浇灌树根,孩子和树一起长大,使孩子从小养成爱林护林的意识。[14]西南少数民族与水(自然)展开一系列生产、生活实践,将他们在与水的长期互动过程中经过观察和总结的知识和经验进行自觉归纳和总结,形成了西南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水生态观和生态知识,千百年来这些生态观和知识经过家庭和社会教育传承,一直发挥着维护生态系统的功能。 二、物质生产促进水具有天然的流动性,水的天然流动性携带着巨大的惯性力,这种流动性和惯性力一旦在瞬间爆发导致的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带有巨大的破坏性。水的流动同时因自然、气候等原因也会因水分蒸发而至旱灾,长期的生产、生活用水缺乏对人类社会具有灭绝性破坏,因此,对于人而言水具有一种不易操控性。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是一种本土生态知识体系,它包括意识、理念与信仰,包括技术、技能与经验,也包括习俗、制度与律法,它不仅能抚慰旱涝等水灾害给人带来的巨大的身心伤害,对带有巨大破坏性的灾害行为本身也能进行一系列防灾减灾的应对。同时,世界万物的生长、存活都离不开水的浇灌,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因其适应自然、因地制宜地蓄水、育水与用水,能够直接促进物质生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最直接、最务实的功能,就是通过确保水能促进物质生产,来保证西南少数民族种的繁衍和社会的发展。 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促进物质生产,首先体现在他们对各种水灾害的防灾、减灾意识、技术与制度创制上。世居山林的云南新平水塘波村彝族腊鲁人,有着一套森林分类蓄养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不仅是其“靠山吃山”的生态适应惯习,而且对其作为山地族群的日常防灾、减灾起着生态维护的重要作用。村寨背后和沟渠两旁的森林有防风固沙的作用,被划为“防护林”而严禁砍伐。水源地森林有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被划为“水源林”而严禁砍伐。离村寨、田地较远沙石林被划为“薪柴林”,要求“砍大不砍小”“留直不留弯”“留壮不留朽”等。还有“用材林”,须经批准才能定量砍伐作为生产、建房等用材用料。[15]如此与自然巧妙融合的森林养护制度,是一种出于理性的制度化创制及其遵行。黔东南苗族谚语说:“山上多栽树,等于修水库,雨多它能吞,雨少它能吐。”[16]苗族因此因地制宜,为了稳固山体,防止水土流失,减少山体滑坡的危险,在山顶广植林木,也涵养了水源。西南少数民族对水灾害的历史记忆与防灾叙事的最大集成,当属西南少数民族洪水神话中滔天洪水对人类的灭绝性场景的叙事及其记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活形态神话的王国,彝、白、哈尼、纳西、傈僳、景颇、土家、羌族、怒、独龙、基诺、拉祜族(苦聪)、苗、瑶、壮、侗、傣、布依、水、畲、佤、布朗、阿昌等3个民族均有古老的洪水神话流传,其分布之广在其他区域实属罕见。“各族洪水神话中人与神的争执,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力的愿望及斗争。从这些洪水神话的内容来看,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各族原始初民期待解决威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中心问题战胜水患灾害。”[17]西南少数民族洪水神话有洪水起源、洪水灭世、人祖再生三个母题叙事,但其中包含了人类为了自身发展越界开发山地、滥捕动物,破坏生态平衡等生态批评思想,因此,神话叙事中为了重修人神关系,人类将洪水起源往自己身上揽,进而以天神的名义进行自我社会道德训诫及其重建,这才是西南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的深层生态意蕴所在。 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促进物质生产的另一体现是灌溉耕作为核心的用水理念及其实践。云南最早的农业灌溉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据考古发掘,在大理苍山之麓发现有陂池遗址。陂池遗址在山麓缓坡,筑有堤坝,可截留雨水和自高山流下的雪水,以浇灌田园[18]。滇池东岸呈贡县小松山东汉早期墓出土的陶质水田模型,呈长方形,长30毫米,宽00毫米。一端是大方格,表示蓄水池,另一端为大小不等的1个小方格,代表水田。池田之间有沟渠相连。[19]大理祥云、弥勒县等地区,有几条明代修筑的“地龙”仍然在使用。“地龙”又叫闷沟、龙沟,即埋于地下的暗渠。“地龙”或为石砌水道,或为无数相连的陶管。短者数百米,长者达10余公里。水道的高端(“龙头”)需选择在高地水源丰沛之地,依靠高水位势能,使水流向灌区。[0]地龙深埋地下,不易遭破坏,经久耐用,偶有泥沙沉积,可放大水冲畅。弥渡农民对此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方法,把鳝鱼放入地龙之中,靠其爬行蠕动疏浚泥沙。[1]从事稻作的傣族,早在15世纪编纂的《景洪的水利灌溉》一书,就描述了西双版纳景洪地区的沟渠管理、灌溉技术等水利实务,是傣族人民长期以来水田稻作水利灌溉实践经验的书面总结。羌族为了灌溉依山就势开掘的高山梯田,往往着村寨左右两旁两股泉水的流向修建水沟,其落差较大,如遇高山峡箐不能开沟的地方则用凿空的横木度水。这种地势高差明显的水沟灌溉系统简单实用,在条件十分恶劣的羌族山区有力支持了梯田灌溉。为了充 分利用水资源,贵州羌族民众还在冬季时就引水入田,水经过长久浸泡、储存起来,田里的泥土便被软化,来年开春时便易于耕作。类似“泡冬田”的耕作方法,在侗族地区也同样普遍。“泡冬田”持续10-1年才“炕冬”一次。“炕冬”就是把田里的水一次性彻底排干,改种旱地作物。[]彝文古籍《尼苏夺节·开天辟地》里,记述了远古彝族祖先垒堤辟田、开沟排水的远古记忆: 生冲大海里,俄谷老龙爷,九千九双手,捡捞海底石,夜间捡石头,白天垒石头。石头垒成堆,垒出大海面。又用海底泥,造化成大地。俄谷老龙爷,八万八只脚,夜里忙踩泥。九千九双手,白天勤抿泥,日夜不停歇。四千年开天,三千年辟地……天与地之间,有四个水口:两个进水口,两个出水口……诺谷小龙儿,金棍抖三抖,凿出了溪沟,围成了湖泊,造好江海,开出了河流。再用棍金棒,撬开出水口,海水哗哗流,平坝绿油油。[3] 在创世史诗带有神话色彩的唱诵里,“八万八只脚”“九千九双手”“四千年开天”“三千年辟地”的数量表述表面上以一种夸张的修辞,暗含众人集体协作的力量象征。哈尼族梯田农耕灌溉依靠大大小小、密如蛛网的沟渠,哈尼族不仅创制了在山区开沟挖渠的巧夺天工的技术,也采用了刻木分水的公平用水的制度,独创了有效管理纵横交错灌溉沟渠的沟长制度。总之,正是极富生态价值的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促进了物质生产,保证了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的持续发展。 三、宗教精神寄托“人类学家认为宗教具有除心理功能、社会功能以外还有第三种功能:生态功能。”[4]西南少数民族以水信仰为核心的一系列水崇拜、水祭祀、水禁忌等文化表征,不仅是其水文化独特存在、运行的特征之一,也是其(原始)宗教性最突出的地方。从某种角度说,宗教生态学的视角成为宗教学与生态学交叉最具学术价值的一个研究领域,而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正是这样一个生态学与宗教学相交叉的研究领域。在一定的跨文化比较范围内,我们可以发现没有哪一个自然物能像水一样人类赋予其如此多的神灵,也没有哪一个宗教拥有如水一般丰富复杂的各类祭祀仪式实践。水的创世情结、创生属性与自然流动性,对于人类社会的至关重要性自蒙昧时期即被植入人类的历史记忆装置之中,同时,人类历史上遭遇的极旱、大洪水叙事数千年来随着洪水神话、古歌不断地被演述,特大灾害的灭世记忆也总不断地在人类心理反复被激活和重植。水可为利,也可为害,水给人类带来的福泽与祸害同时存在,一方面,直至今天人类为了维系人-水和谐的关系一直在不断地探索操控流水与合理用水的理念、技术与方法。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水带来的更多润泽和福祉,同时为了战胜旱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涉水灾害带来的心理恐惧,西南少数民族最后将水神化进而对其顶礼膜拜。水神祭祀、祈雨仪式以及各种水禁忌,都以神圣性宗教祈愿、祈福与禳解,表面上对涉水神祇表达崇敬和祭拜,深层次的功能却直指人内心深处的精神寄托,即祈求雨水丰沛与安抚水害恐慌的功能。 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的宗教精神寄托功能,出于少数民族对天然流动而不可控的水进行控制的心理需求。面对自己难以掌控、可能带来旱涝等灾害的自然水,人们将它进行神化处理笃行自然崇拜,虔诚崇拜起附于其上各种各样的涉水神祇,认为以此与自然水(神)进行一种神圣的交流,换回其与人的一种合作与友善的融洽关系。基诺族世居山林,不仅有着严格的山林管护制度,更有着严厉的神林禁忌。任何人擅自进入砍伐神林将遭遇不幸,因此,基诺族社会无人不对神林心怀敬畏,人们不敢冒险入林,更不敢妄动其一草一木,神林至今保持着原始风貌,其生态保护的效果十分明显。拉祜族盛行自然崇拜,几乎每一个拉祜族村寨都有基于山林的山神崇拜。如遇天旱或雨水成灾时,他们会自发前往山神庙烧香点蜡祈祷,据说祈祷后很灵验。山神庙所在山林严禁砍伐,否则将遭灾。在拉祜族的原始宗教观念中,神山、神树均位于水源上方,没有树就没有水,这些空间均严禁开荒、砍伐,客观上起到了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5]绿春县坪河乡车里村一带自称“格角搓”的哈尼族,献祭河水神时,以一条黄牛、一只公鸡和少量的姜、盐、茶为祭品,由摩匹祭司各取一点倒入河水中,并念诵道:“龙神,我们用牛牲、鸡牲奉献你,求你不要发洪水做泛滥,毁坏五谷庄稼,冲走六畜牲口”。[6]侗族以水稻耕作为主,自然崇敬水神,“他们对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岁首都要敬祭水神,在这一天,妇女到水井或河里打水,必须先到井旁或河边点香烧纸,然后才能取水回家”[7]。西南少数民族认为山神、林神、树神、水神、龙神等一系列涉水神祇,均为附在水这个不易控制的自然物的超自然力量的幻化形象。不能心怀敬畏地对它们进行虔诚的崇拜和祭祀,不仅达不到掌控水的目的,还会带来旱涝以及山体滑坡、水土流失等一系列次生灾害,而且还会带来村寨不顺、瘟疫流行等相关劫难。因此,这种集体祭祀事关村寨、族群整体的物质和精神利益,更是建构个人对水害、水患以及相关灾祸的一套精神防卫术。 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的宗教精神寄托,也出于人们趋吉祈福的用水需求。拉祜族在每年冬月十五均要举行祭水神活动。届时全村凑钱买猪献祭水神,祭祀辞为:“水是养育全寨人的奶汁,我们不忘水神的恩德才买猪献祭,祈水神保佑全寨子子孙孙有水吃。”完毕后猪肉由全寨人共同分享。[8]这完全是对水的实际需求上升为一种心理投射,犹如奶水的水是全寨人的命根,祭祀水神就是为了保证有水。滇南彝族尼苏民间咪嘎哈祭祀当天早晨,先要祭祀“依堵塞”水井神。村寨祭祀由毕摩主持,在水井边献上公鸡、母鸡、酒饭茶等祭品后,要念诵《祭水井神经》: 我们全村人,来到高山顶,看来松树枝,采下松毛来,松毛来洗井。砍来林中竹,竹叶来扫井。情节的净水,有翻水螃蟹[9],翻水螃蟹,犹如俏姑娘,一天翻九次,一天翻九回。清澈的泉里,有管水的田鸡,恰如俊伙子,一天放九次,一天放九回。清秀的井中,井中有花鱼,就像勤劳儿,一天扫九次,一天扫九回。石缝唐出水,清洁又甘甜;石笋流出水,清秀有甘美……来把井神祭。寨头清洁泉,村头清澈井……清泉的泉水,清澈的井水,时时淌净水,天天涌甜水。[30] 这里,彝族尼苏人祭祀水井神首先要清扫、清洁水井,这对应着水井常年流淌泉水的清洁与甘甜,同时整个祭祀的物质功利目的则在于保证泉源不断,提供村寨生活用水。但是,这个深层的物质功利被披上一层原始宗教的外衣后,才能首先从人们的心理上对物质功利的诉求得到满足和确保。 哈尼族的“夏赫候”,意为祭田水口。每年农历四月田里秧苗发蓬时,各家择日,用一对蛋(鸡鸭蛋各一)和糯米饭等物品祭献自家稻田水口,其目的是希望田里的秧苗无灾无难,快快成长起来,金黄色的谷子象沙石一样饱满。[31]这是从水延伸到了水作稻谷的长势,后者的生长和丰产依靠前者的灌溉,有了水的滋润和浇灌,希望无灾无难顺利成长、丰收。贵州惠水县摆金镇冗章村有一口古井名“马鞍井”,当地苗族将其视为“神井”。每年均以鸡、刀头肉给神井祭祀。若遇天旱,全寨苗民就去井边祭供求雨。[3]在台江县交下苗族村寨,春季属龙的孩子必须拜祭水井。当地人认为春季是雨水季节,带孩子祭拜水井,可使属龙的孩子心性稳定,以水井作为稳住孩子的栖息之所,愿他身心健康。偶里苗寨风俗中,新年初一凌晨家家户户要带上香火、供品到水井祭祀,然后取水回家,煮开泡茶敬神,以祈求新年平安顺利。[33]西南少数民族将旨在用水的水神祭祀推广开来,在求雨、保水源的主要目的基础上,由水的关涉性增加了祈丰、祈福、长寿等相关祈愿,这是对水创生属性的一种神化及其泛化,充分寄托了人们对水的一种普遍的宗教精神依赖。因此,在西南少数民族所有涉水的祭祀仪式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至关重要的,参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丝毫不能马虎,在宗教实践中“心诚则灵”是一条通行的原则,所有的严谨和严肃都是为了确保仪式最终的灵验,而这个灵验结果的指向是人们的内心深处。 四、民族文化传承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文化的创制与传承本身就是民族文化传承的过程,水文化的传承具有民族文化传承的功能。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不是一般形态的文化,它自身犹如水具有吸溶性一般包罗万象,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应对水环境的意识形态的文化观念,作为直接处理和解决各种治水、用水等一系列水问题的理性创制总结的技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社会内部整体协作和自我管理手段的水制度,以及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道德和审美的水哲学理念和认知方式等,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的这种圆融性特点,使它甚至从物质、精神与制度等多维度与民族文化系统本身的结构及其运行相并行。水自古对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不可或缺性,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水,因此,作为他们长期以来适应自然、应对水而创制、传承的一套理念、技术与方法的水文化,自然融入其民族文化及其实践的方方面面。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不是一个书面化的系统知识,它一直以一种活形态的方式与自然(水)相融形成自己独特的运行体系,它渗透在西南少数民族日常生产、生活空间几乎每一个角落里,随着他们围绕一系列的水事活动而展开的身体实践发挥效能。这样看来,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的传承,完全是他们生活中一种自然而然的传承,这种独特的生活化体性传承从心理开始,口传心授,在生活现场完成代际间的顺势传递。西南少数民族水事活动涉及所有族群成员,水文化融入民族文化的体系之中,所以,水文化的传承自然也实现了民族文化的整体传承。 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根性文化,水文化的创制与传承保证了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根性文化,西南少数民族首先在思想认识上对水文化异常重视,这种认识一经达到一种神圣的宗教观念后,常常被置于一个至高的地位。在普米族的宗教生活中,韩规教、藏传佛教、释毕教三大宗教并存,其中韩规教影响最大。普米族韩规经《查子恰打》记载: 出行不要惊动山神、水神。过往森林间,不轻易用砍刀折断树枝;见到小鸟不去捉,要想到蚂蚁、蝴蝶都是有生命的,是可怜之物,不随意去伤害它们;从水源上跨过,亦要想到别人还要喝干净的水。[34] 山水林木、鸟蚁蝴蝶都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拥有平等的生命权,惊动、伤害它们,就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禁跨水源的禁忌,则出于协调社会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以整合一种基于社会道德的超个体的公共利益。可见,西南少数民族文化随着自然生态,以其宗教戒律的形式得以“神管”,同时,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往往还以族群集体共商议定的民间规约的方式实施“人管”。在这一方面,西南各个少数民族几乎均有自己的民间规约与习惯法。侗族地名多以“洞”(“峒”)、“坪”“溪”命名,侗语“洞”,指同一水源的小灌溉区,而分享同一水源耕作稻田的大都是同一家族的成员,这种以共享同一水源组建而成的村寨聚落往往构成一个“洞”。侗族“款词”说:“讲到田塘用水,也要合情合理,共源的水,同路的水,公有公用,田塘有利,大丘不许少分,小丘不许多给”。[35]相似地,始于明朝的瑶族石牌律则以书面成文法的形式予以正面规约。如《三十六瑶石牌律》指出: 我们二十四花山,我们三十六瑶村,三家为一村,五家为一寨,小村靠大村,大村靠石牌。天下有百种粮,世上有百样人……人心隔肚皮,防范不可忘。这样,才砍树置牌;这样,才杀牛立牌,才制十二条“三多”[36],才定十三条“俄料”[37]。有了石牌话,瑶山固如铁。石牌大过天,对天也不容。哪个敢作恶,哪个敢捣乱,即使它是铜,也把它熔了;即使它是锡,也把它化掉。[38] 砍树置牌的瑶族石牌律中有很多诸如育林、护林与保水、护水等有关自然生态保护方面的内容,“石牌大过天”,在石牌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在民间宗教与律法神圣与世俗两方面得到很好的传承与保护。 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源生文化,民族文化体系任何一个方面的运行几乎都少不了水文化的参与,故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水事活动而得到传承。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渗透入西南少数民族哲学、宗教、语言、文艺、技术、规约、工艺、游艺、饮食与服饰等民俗表征,水文化犹如一条主线串起了这些民俗文化的散珠,而串起散珠靠的是作为实践行为的一系列水事活动,不论是神圣的祭祀还是务实的治、用水与管水。云南红河县车古村和绿春县牛孔四大寨彝族尼苏人,在二月咪嘎哈祭祀当天晚上,女子要跳“栽秧鼓舞”(亦称“丰收鼓舞”),男子则在旁围观。该鼓舞源自彝族洪水人祖再生图腾崇拜,是对彝族远古祖先历史记忆的一种艺术化蹈舞。其来源传说讲述: 很久以前,第一次洪水泛滥时,人类祖妣俄玛和俄倮姐弟俩,按天神策格兹旨意,上山伐红椿木,挖空树心,做成树桶,然后用椿板把树桶口蒙上,并用蜂蜡封死缝隙。俄玛和俄倮姐弟俩躲进树桶里避洪灾。洪水逐渐退潮干涸,树桶随洪水退潮逐渐下降。树桶落地,姐弟俩钻出树桶,但世间万事万物都被洪水灭绝,千山鸟飞绝,万里无人烟,后又遵天神策格兹旨意,姐弟俩结为夫妻。从此他俩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繁衍子孙后代。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拯救过祖妣的俄玛俄倮姐弟俩的椿树桶,杀黄牛献祭,并将树桶的两端口,蒙上牛皮,做成牛皮鼓,人们围着牛皮鼓边击鼓边手舞足蹈地欢庆娱乐,娱祖娱人。祭鼓庆鼓跳鼓舞即栽秧鼓舞就流传了下来,并慢慢形成了至今规范而婀娜多姿、欢快热烈的栽秧鼓舞。[39] 跳鼓前,毕摩取清酒祭献牛皮鼓,神情庄重地念诵祭祀辞:祖宗定规矩,我们要履行,鼓不是我敲,是阿龙[40]先祖来敲。先祖阿龙神,保佑五谷粮,保佑人畜禽。祭毕,将酒倒在鼓身上,以示让先祖阿龙神喝饱酒,毕摩悄然离去。随后,女子们女扮男装,或披蓑衣,或着新装,或戴面具,或披花毡,或佩戴象征男子生殖器的葫芦……他们或两人同舞,或多人同舞。鼓舞套路繁多,鼓点固定,以形象的动作表现出从犁田、耙田、撒秧、拔秧、插秧、薅草,到割谷、掼谷、背谷归仓等一整套稻作生产的过程。[41]鼓舞本为纪念祖先再生的历史,后来人们将其附载了稻作生产过程的身体展演,是一种以巫术互渗律原则从人类自身的生殖求子到稻作生产、丰产的过渡。滇南彝族咪嘎哈是一个典型的忆祖涉水祭祀,它从洪水人祖神话叙唱、宗教祭祀,到艺术化鼓舞展演,以及包含了彝族服饰、饮食、游艺与(禁忌)规约等相关民族文化要素无一不包,以一种文化集成的模式集中共时地实现了民族文化的整体传承。 五、地域社会整合水文化是长期的人地互动后形成生态关系的人类社会的智慧结晶。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是西南少数民族数千年来应对西南独特的水环境地域而创制、总结得来的一种集体生态智慧。水资源的公共性与开放性,使得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带上了一种公共性与集体性,而水文化的公共性与开放性最直接的体现是水事活动的公共性与集体性,这一可能源于西南少数民族古老的原始共有制的文化遗存惯性,一源于水事活动一般多为大型社会文化与工程技术活动,单凭个人的力量在哪个时代都是绝不可能完成的。因此,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天生具有吸纳、内聚、团结、协作的精神内涵,它通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集体水事活动,发挥着一种旨在凝聚各个成员的综合性整合功能。由于祖祖辈辈共享相同的水域和流域,以这些水域、流域、水体为中心,在西南自然地域空间历史地形成了诸如金沙江、古蜀平原、澜沧江、滇池、红河、珠江、长江上游等流域民族文化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具有一种更大范围内的整合功能,包含族群整合与地域整合。在现实而具体的生活语境下,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的族群整合与地域整合,不是截然两分的,它们之间既相对独立,又时有交集。 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族群整合功能的发挥,基于水文化所隶属的具体的相对地域范围,以及各个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境遇和心性特征,后者似乎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特别指出:“蛮治山田,殊为精好。”哈尼族开垦山地梯田进行稻作,在唐代就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清嘉庆《临安府志·土司志》描绘了哈尼族梯田农耕的景象:“依山麓平旷处,开凿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至山势峻极,蹑坎而蹬,有石梯蹬,名曰梯田。水源高者,通以略(卷槽),数里不绝”。很难想象,层层万仞梯田,数十里的渡渠,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灌溉沟渠,如果不依靠集体的力量共同协作,如何实现开垦与耕作。哈尼古歌《开田种谷》篇唱到: 一个人力气再大,也开不出一架山,十个人力气再小,也开得出一道岭,开荒山的人,要像鱼抢水一样挤,埋草籽的人,要像蚂蚁抬食一样齐心。睡在十棵树上的兄弟叫拢了,缩在十个草窝的姐妹叫齐了,大家伙合一处,来做开山的事情……十个合声的汉子说话,十张嘴说出一样话,十个合意的女人做事,十颗心想成一颗心。[4] 这是梯田起源古歌中对远古哈尼族先民集体开山造田的历史叙唱。古歌中说哈尼族开凿梯田是受到牛、猪饮水、打滚的仿生启发,但是其中强调得最多的是族群集体团结、协作的力量。正是通过开山造田、开沟挖渠、刻木分水、逐田灌溉以及护林育水等一系列水事活动,哈尼族作为一个古老的迁徙民族将平坝稻田耕作技术创造性移植到山区,成为山地梯田稻作的杰出代表。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哈尼族成员都被自然地吸附、凝聚和团结起来整合成为一个民族群体。如今,哈尼梯田以其古老的人类生态智慧荣膺“世界文化遗产”景观,这又反过来振奋了哈尼族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使其在民族文化上比以往更加凝聚。“对民俗的传承与享用,以一种潜移默化的生活方式进行,族群成员甚至都没有感觉到,就在自然而然的参与中实现了。同时,民俗也悄然地将一个个成员吸附、凝聚、团结在一起,整合成一个稳固的文化-社会共同体。”[43]正是哈尼族围绕梯田耕作的水文化这个民俗传统,使哈尼族整合成一个稳固的文化-社会共同体。 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作为扎根于西南独特自然地理空间的一种具有普遍生态价值的地方性集体智慧结晶,在西南少数民族水生态共同体视域内的水文化具有整合地域社会的功能。“一条河流,一条水渠,不可能只流动于一个村庄内部。它所流过之地,人们形成群体保护自己的利益,到为了共享资源和协作,有不同利益的不同群体又需要结合成为一个超过村落范围的合作圈子。”[44]水资源共享与水事活动协作,使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超越其族群性而上升到一种族际互动的地域性,这是水的自然流动性所带来的公共性和共享性的集中呈现。虽然有时为了争夺水资源,村寨与村寨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会有纠纷与冲突,但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西南少数民族分享一个相同的水生态共同体,族群关系基本上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由此,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因水而合”获得一种地域整合。因面对相同的自然水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域社会的西南少数民族,同时分享着一些相同的水文化。无论世居坝区的壮、侗、傣族,还是迁徙山区的苗、瑶、哈尼、彝、拉祜族等都从事稻作生计,开沟挖渠、渡槽输水、车水移水,以及刻木(石)分水等用水规矩基本上都比较普遍。尤其是刻木分水的制度,也称为“水平”“水秤”,有效减少和平息了地域社会内部因水资源分配问题而可能产生的纠纷和争斗。西南少数民族认识到山林在涵养水源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也普遍笃行神林祭祀为核心的水崇拜。傣族的竜林,佤族、拉祜族的神林,彝族的咪嘎哈林、密枝林,哈尼族的寨神林,苗、侗、瑶、怒族的神树等,通过集体祭祀以神灵的名义得到了严格的生态保护。将水的创生属性进行一种认知论的系统总结,西南少数民族普遍存在水生型创世神话。“千百年来,时代屡经更迭、风尚不断变迁,水生型创世神话所包含的生殖力、生命力信仰却始终存活于南方民族多种民俗之中,延绵不绝。”[45]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地域社会整合的功能,是一种水生态共同体内协调族际、村际之间的社会功能,对于建构一个当代族际共享的和谐地域社会具有重要的社会生态价值。 结语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的生态维系、物质生产促进、宗教精神寄托、民族文化传承与地域社会整合等多重功能,是我们基于功能主义论的一种学术归纳和解析,在西南少数民族现实的水事生活中,上述多重价值处于同时发生并一起发挥生态效能的联动态势,它们作为一个结构性整体功能存在并真实产生相应的动态社会影响。在所有这些功能中,自然生态维系是根本,它是西南少数民族通过创制和传承独特的水文化来适应水环境、协调并建构一种和谐人-水关系的终极追求。物质生产促进是基础,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依靠物质生产来保证人类自身的生产,这也是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最务实、最世俗的功能。因此,不论物质的、精神的与制度的水文化,首先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物质生产对水诸如饮用、灌溉、防灾与净化等一系列物质生活需求。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的民族文化传承功能,在于水文化在民族文化体系中源生根文化的首要地位,通过相关水事活动“因水而传”民族文化也就再自然不过了。宗教精神寄托功能,是西南少数民族对水的一个有关心理安抚的较高级需求的满足。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宗教仪式的源头,应该是其对物质生产的一种深层心理诉求,在对涉水神祇的集体性祭祀仪式中作为一种现场心理震撼和精神振奋同时出现,能够很好地实现其精神寄托的目的。但同时,正如埃文斯-普理查德所说,“并不是仪式的被规定的目的向我们透露了它们的功能。它们真正的意义在于,首先,仪式将氏族的人民集中在一起,其次,在集合的场合集体性地举行仪式可以在氏族的人民中更新其团结感。”[46]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以涉水神祇祭祀仪式为结构存在的宗教实践,以非常态的方式使族群成员日常常态下被有意无意疏离和消散的团结感重新得到了强调和更新,由此,不仅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族群得到了认同,而且作为一个更大单位的地方社会也顺势得到了整合。因此,传承和保护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正是要确保持续发挥水文化的这些原生功能,尤其是自然生态维护与地域社会整合等,一能为当前人-水紧张关系的缓和有所启示,一能为当前边疆民族团结、生态和谐社会的养成提供借鉴。同时,也要集思广益,创新思维,结合新的社会语境,创造性转化和开发诸如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遗产观光旅游、水文化生态产业开发等一系列新的功能。 (原载于《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年第4期)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feizhouxiangdx.com/jdhwh/2053.html
- 上一篇文章: 陈皮的翻晒,这些姿势你get过吗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