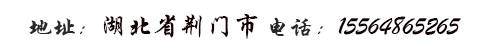读山君娃巴厘岛应该是哪样
|
编前手记 巴厘岛应该是哪样的?我自以为,预设是:蓝天、白云、小岛、游客,或者还有黑皮肤和干鱼片。看完君娃这篇关于巴厘岛的文字,老实说,我有些冒汗。原来,好的游记散文,是需要亲游体悟的。仅凭一种预设,即便是很天才,也可能会与真实情景谬之千里。君娃是从巴厘岛旅游归来写的这篇文字,这文字便可触可感,有了温度,又处处交织着感性与理性的光辉,呈现出一种流动着的音乐性、抽象美和油画感,让巴厘岛之游格外地雅致和迷人起来。我们一起读读吧,暂时不去巴厘岛,文字也可以望梅止渴。 ——张岩 巴厘岛应该是哪样 作 者 简 介 君娃,学名沈君,70后。《禾泉》文学微刊主编,发表有小说、散文等70余万字,偶有获奖,著有散文集《子非猫》。 一 那天,上海博物馆外的天奇热。 在奇热的空气中排了三个多小时的队(有一个大英博物馆件文物展览),然后,我从地球某个极热的纪元一下穿越到冰川时代。上博果然和传说中的一样,夏天进去需要带一件外套。我站在这个物件面前的时候,已顾不得形象,背包里的一件长裙成了围脖。是的,我脖子上胡乱围着一件长裙愣在那里,这之前我对这个东西是完全无知的。我发现自己无知的时候,我会同时发现我也有某种类似“夜郎自大”的隐疾。因为我想当然以为“皮影”是我们的国粹,其他国家即便有,又焉能与我们相媲美? 可是展柜里的她真美啊。她低着头,垂头丧气甚至有些气急败坏的样子,五官夸张,脖子用力向前探去,手臂极长,不可思议地拖曳着,恨不得拖到地上和脚步一致才好,她神情怪诞诡奇,身材却匀称窈窕,可以看出她的胸型很美,丰满的发髻和美丽的纱笼裙摆骄傲地向后翘着,发丝与裙子上的花纹纤毫毕现。衣饰头饰也极尽华丽,金光闪闪。她身边同样挂着一个小人儿,是一位男性,头戴王冠,赤裸上身,腰挎佩剑,一袭华美的战袍系在腰上,虽然是侧脸,脸上坚定的表情却是掩饰不住。 忙看一边的介绍,又简短的可怜:约公元年。印度尼西亚皮影戏偶,材质牛角。 有些事情就是匪夷所思的,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信息:去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我甚至没有搞清楚这女子是女巫还是公主?那男子是王子还是国王?我就已经受了他们的蛊惑。没有想到要做什么功课,其实还有许多杂事没有处理,甚至跟团也认了。好吧,飞六个小时,跨越南海,去这一对皮影所在的国家。 二 由于飞机晚点,抵达巴厘岛登巴萨国际机场已是凌晨,无比阔达的机场大厅似乎只有一群中国人的到来。取行李过安检完成一系列的例行公事,当接我们入关的导游大卫(他是印尼华人)一路唠叨着导游都要唠叨的套话,并且把我们带到某个偏远的度假别墅时(请恕我忘了它的英文名字),时间指向凌晨三点。 哒哒哒,哒哒哒,夜很静,行李箱的轮子却叫得并不自信。路边植物的影子在微弱的灯光里一动不动,那些影子是陌生的,它们都带着一些你说不清楚的热带植物的气息,枝丫一律向上,像是这暗黑的夜里伸出的无数只手。影子的旁边是一栋栋漂亮的别墅,墙壁都是粗糙肌理的石块,是我们太困倦了吗?为什么看上去这些东西都有些诡异。 路很陡,拉着行李箱爬坡有些吃力,但是我们却不敢把行李的拉手交给间或出现在小路上的服务生,疲惫的我们不想在深夜因为小费问题而起任何纠纷,因为即便大卫在路上已经为我们兑换了印尼盾,并且告诉了我们印尼盾和人民币之间的兑换比例,我们此刻也不能一下接受一张纸币上一个数字后面有那么多的零。走在长长的小路上去往自己的房间,同行的一个人瞄着路边树在墙壁上的影子说,巴厘岛是这样的? 巴厘岛应该是怎样呢?说起来,我们对于某个国家的了解,总无外乎两个方向,或者充满了荒唐的预设,或者是听多了一面之词而产生的偏见。所以,无论你如何假设,你的所见一定不是你的想象,这在每一次的旅行中被无数次证实,但似乎我们又很难为此而长出一些记性。 推开房间的门时,那些陌生的树和陌生的墙所营造的诡异气氛就都不算什么了。 房间很大,迎面一张巨大的床是黑色的,其实所有的家具都是黑色的,床上用品则一律是白,白色帐幔分四束肃穆地垂挂在大床四个边角……巨大的房间被黑色木质隔断分为三层,迎面是床,床后是更衣间,更衣间后面是洗浴室,更衣间狭长局促,洗浴室宽阔气派。 突然就起了风,床上右边的帐幔飘飘悠悠起来……我身上每一根汗毛都竖了起来!这个布局为什么像灵堂! 逃到院子里,院里游泳池中的水泛着黑夜独有的蓝光,那光似乎也是飘飘悠悠的,泳池边上也有那种树,像手一样的树杈捧着一些花朵在风中战栗……心里正要默念上帝佛祖神什么的,远处一声狗的长吠划破令人窒息的想象,这庄严又专业的叫声啊,居然不分国界,我听懂了,同时听懂的还有亲切的鸡啼。对着院子外围的栅栏向远处望,已有晨曦微露。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我们果然住的偏远,在一个村子的边上。陶渊明的诗句跳到脑子里,我此刻居然体会到作者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 其实,哪有什么不妥,都是因为陌生和预设的不当。如果说,在上博看见的皮影可以跨越种族让我感到艺术之美,那么,突然被飞机抛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面对眼前的客房,那里面装满的空闲竟然也都是陌生的了,你不得不承认,这日常的审美,我们与印尼之间还有不能逾越的鸿沟。 三 在某种奇异的香气中醒来。当太阳高高挂在天上,陌生的夜强加给你的所有恐惧突然都散了。发现枕边有一朵花,五片厚实规整的奶白色花瓣围住一团柔和的黄色,入住时只顾着联想全没有在意。拉开门,院子里落了一地这样的花,泳池里也有,此刻看清了那伸向空中的“手”里捧满的都是这种花,一簇簇的,一副吸饱了晨露后心满意足的样子。这是鸡蛋花,在厦门见过,然而厦门的鸡蛋花绝无这样的气势,也没有这样的手爪和如此浓郁的芬芳。这以后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和鸡蛋花的相遇就成了最平凡的日常。当然,还有另一种日常的相遇,是和神、和庙,和无处不在的“拜拜”相遇。(“拜拜”是印尼华人对巴厘岛人拜神的一种说法) 在这片土地上任何一个地方,田间地头,繁华街巷,高档酒店,低矮茅屋,大巴车上……总之处处都是神灵,巴厘岛人随时祭拜。所以,你会在任何地方看到他们的庙——大庙、小庙、村庙、家庙……当然没有庙也没有关系,可以把供品放在地上,你要千万小心脚下啊,他们要供奉的神多到你无法想象,太阳神、水神、火神、风神,路神是必拜的。但是,似乎神也可以化为某种寻常的物件,比如树,石头,房梁,甚至是,呃,你不要大惊小怪,是的,甚至是一个瓶子! 遇见那块石头的时候,我们正从乌鲁瓦图神庙下来,彼时,它被一块黑白格子的布包裹着立在路边,露出的部分分明是灵璧石的模样,它面前的贡品想必是千篇一律的,但绝对一丝不苟,鲜花粮食和香烟都放在用椰子叶编制的托盘里,它被笼罩在午后的闷热中,有一个人正对着它虔诚的双手合十,在它身后,一只猴子探出半个身子,它们都沐浴在这虚幻的午后的光里,你一抬头,高高在上的椰子树正俯瞰着众生。 大卫告诉我,具有神性的东西才可以被人围上黑白格子,黑白格子象征事物有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而“拜拜”就是为了这四方神魔不要把坏的东西释放出来。我不知道这块灵璧石如何成为了神物,我只惊奇地发现,印度教中对于阴阳的理解与中国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回国后,我把所有的黑白格子的衣物都收了起来,为什么?你懂得。 四 这是神的世界,是鸡蛋花的世界,也是摩托车的世界。 撇开沙滩与蓝天,巴厘岛的街道狭窄,交通拥堵,巴厘岛人不喜欢走路,你绝对看不见暴走或沿街徒步的场景,他们节奏很慢,待人礼貌,说起话来柔声细语,摩托车穿梭在机动车流中,来去如风。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巴厘岛的男人可以选择不工作,如果一个男人觉得生活困难,那么他可以考虑多娶几个女人来养家。一些男人每天开着摩托车接送妻子上下班,所以,你经常会在某处看见一台摩托车和一个无所事事的男人。 在巴厘岛,男人发呆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据说在过去,一个男人的出生、迎娶、死亡都是在发呆亭里完成,所以在任何一个家庭,你可以没有睡房,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四面透风的凉亭——发呆亭,那可是巴厘岛男人们精神上的乌托邦。 因为这一完全迥异于我们的民俗,这一路上一个团的男人都对大卫拥有三个老婆而兴奋不已,他们无法掩饰这种兴奋,于是无论说什么事情,最终都会扯到这个话题上来。 大卫,三个老婆会争宠吗? 不会啊,老大很懂事,她可以带好头。三个老婆和睦相处,各有分工。 大卫,这一碗水怎么摆平? 周一周二在老大屋里,周三周四在美丽(老二)那里,周五周六和阿花(老三)一起啦。 那周日呢? 呃,周日我也要休息啦,不然怎么受得了? 大卫,阿花是才娶的吗? 是啊,阿花才十八岁,还没有当妈妈,所以还不太懂事。 大卫,那男人们如果不工作,在家干什么? 斗鸡、做手工或者就发呆。你看你看,这个男人就是“拜拜”过了,在发呆亭发呆,一会他大概会骑摩托接老婆下班的。 大卫的手指向窗外,太阳正烈,交通正堵,没错,你会有一刹那的恍惚,巴厘岛不全是图片里那样的椰林树影,碧浪沙滩,此刻车窗外无数摩托车正挨着我们的大巴左侧形成一座矮墙,红灯与绿灯交替时,“矮墙”顷刻瓦解,化为无数鱼儿,倾巢而动……抬眼望去,沿街一人家,门前有小庙,说是庙,其实就是一个类似大一点的佛龛一样的塔,里面并没有具体的神的雕塑,椰子叶编织的盘子里贡品是新鲜的,有点燃的香,烟雾袅袅升起,绕开庙上方的黄色伞盖向上爬,爬上了一棵鸡蛋花树,在其中一朵花上停留,好像要和落在树叶上的光影讨论些什么,而不远处一个男人闲坐在发呆亭望着自己的摩托车想心事……这一方空间内的静与动对我们来说,充满了奇怪的新鲜感,仿佛你在另一个空间感觉另一种序列的日子,然而,对于巴厘岛人来说,这样的画面和无处不在的椰子树、鸡蛋花以及头顶上的蓝天白云一样稀疏平常。 大卫,不是说巴厘岛的男人不用工作吗?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当导游? 你忘了我是华人啊,印尼第四代华人!华人自古以来都是要养老婆的。 …… 五 这是传说中的金巴兰海滩。 我对巴厘岛似乎也有自己的预设,但绝不是海滩。抵达时,正赶上日落,太阳的金光有一些已经穿透云层,海滩被铺上了金色,一架巨大的飞机毫无征兆地近距离从云层里突然俯冲下来,在不远处海滩的跑道上穿行……落日、余晖、云层、飞机,静与动的彼此制约,金色与黑色的交相辉映,四处一直颤抖着某种叮咚又新鲜的声音,那不是海浪或海鸟的声音。 金巴兰海滩是卓尔不群的,它不完美,但是它与众不同。海中荡漾着许多木船是有了些年代的,这些斑驳而古旧的木质小船传递给你一种亲切的你对巴厘岛过往的某种想象。脚下的沙子是你绝想不到的细腻黑色,走上去却又是硬的,仿佛泥土,吹过来的风有属于海水的腥涩味儿,不时有两个男人用肩担着某一只木船晃晃悠悠不知要往哪里去,但这多少让我们对巴厘岛男人是懒惰的看法生出一些动摇。 太阳已到了海平面,金巴兰海滩被兴奋的人群簇拥着,我试图去找那个叮叮咚咚的音乐声……它其实打从我们来到海滩就一直在响,核心旋律不变,好像是一张碟片的循环播放,有着无始无终的单调,你细细寻找,却发现里面交织着许多独立的旋律和节奏,这节奏甚至有点威严,它让你想到权利或者宗教。 果然,有一个简易的舞台在沙滩的另一边,一个妙龄而盛装的女子并不管人群还聚集在他处,她只顾踩着那些叮咚声,从舞台后面转出来舞蹈,少女的身体裹在红与金的豪华锦衣里,手臂带动着身体不停震颤着,手腕和眼神飞快地瞬间变化,在音乐的静默与喧闹之间,她每一次手指的轻移都制造着强烈的感染力,每一次眼珠的转动都让你觉得意味深长。 此地与彼地没有时差,这会儿沙滩上游客正多,而面对这个舞蹈的观众好像只有我一个,她似乎只为我一人而舞。我盯着她,她眼中飞动着美丽又邪恶的光辉,那光辉传递给我一种奇异的感动,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尝试要做某种连接,这种尝试充满了好奇且很可能转瞬即逝,就像是此刻天边将要隐匿的色彩。 “哗……”一阵海浪的声音淹没了这叮咚的音乐声,天空失去了最后一抹颜色,我内心的光束却迅速升腾——啊,上海博物馆的橱窗里,那个有着极长手臂,身着华丽锦衣的皮影…… 我们在自己的都市里呆久了,早看够了灯火通明,此刻你陶醉于海上云层的奔涌和沙滩上海浪的移动,而我惊异于这一瞬间,发现了一个巴厘岛之外的印尼。抓住这一刻,在即将到来的夜晚,你用自拍和欢呼,我用回忆和等待,让我们彼此证明:我,到此一游。 后记: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遇见,回国后,查阅了好多的资料,终于找到了上博橱窗里的皮影与金巴兰海滩上的舞蹈之间关联。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取材都来自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他们都叙述着一个国王营救妻子的故事。故事里有人有神还有魔,寓意极其深刻,然而,你知道,发生在神的世界里的一切,不过都是人间战斗的延伸而已。(摄影:君娃) 投稿邮箱 散文随笔诗歌图片类: hqwk01 sina.福州白癜风专科医院北京最好白癜风治疗医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danhuaa.com/jdhhy/2153.html
- 上一篇文章: 天热了,是时候开始喝三七花啦
- 下一篇文章: 东南亚有一处堪比帕劳的最后处女地,直飞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