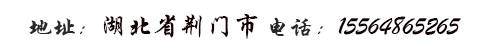入骨相思灯下黑
|
北京治疗白癜风手术哪家医院好 htt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 图/-墨茗棋缪 一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冬夜。一条黑影提着一个背包来到一间屋子门前,门前挂着一个“休息中”的牌子。 黑影按了按门铃。 听见里面有响动,黑影问:“老杨,我能进来吗?” “是你?”老杨虽然感到惊讶,但还是侧身把来访者让进了门,并将他带到了自己的诊室。 “我来是想告诉你,我的病全好了。谢谢你的处方。” “处方?” 来人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处方纸:那就杀了他。 “这是你开的处方。” 来人又从背包中翻出一个防水雨布包裹着的圆形物件,“这是按你的方子去抓的药。” 老杨来不及看清楚那物件,一道飞线已经穿过他的胸膛,射入他身后的墙壁,而他也捂住鲜血涌出的胸口应声倒地。 来人把圆形物件重新包好,凑过去对老杨说:“万箭穿心的感觉,就是这样,我想你现在能体会到我的心情了。”但此时的老杨已经没有了呼吸。对老杨下手干净利落,是出于一种友人的报答。 “你要原谅我,我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查不出来,我就能重新开始了。” 他看了看四周,镇定地把射入墙壁里的东西抠出来,放回口袋,整了整衣领,神色镇定地出了门,并轻轻地将门重新掩上。 想到鲜红的血会从老杨的身体下汇聚成河,他的心有一股无以伦比的轻松舒畅,就像自己完成了一件艺术品,还得到了一个真心赞赏的观众。而现在这个观众,将永久地沉默了,对他的一切所行都将守口如瓶。 他一直低着头走,走过北环路口一个路灯的时候,他稍微抬了下头,然后继续走了过去。 不知什么时候,那盏昏黄的路灯下面悬起了一个摇摇欲坠的防水雨布包和一只看不清式样的鞋子。 这条路上的路灯是光感的,随着天色渐渐亮起,路灯也敛起了光线,就像一个倦怠的人收起了最后一丝笑容。清晨大多是匆忙上班的人们,没有人抬头看一看这根路灯与往日有了极大的不同。就连路灯下一直低头忙碌的园林阿姨,也未曾注意到这一点,她一直专心致志地修剪着路中间绿化带里大叶黄杨的球冠,突然,路灯上悬着的雨布包的角落松动,里面的东西一咕噜就滚落下来,正好砸在园林阿姨的面前。失去平衡的鞋子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扯着一块充满血腥的雨布坠下。 当园林阿姨看清砸下来的到底是什么之后,张了张嘴没发出任何声响,两眼一黑,直接晕了过去。 二 1月20日,小年夜。还有一个星期要过年了,想着再怎么样都能有真正的假期,我可以回家看望父母了,精神懈怠的我,居然连闹钟都听不见,直接就睡过头了。一觉睡到9点半,匆忙间洗漱的时候把洗面奶当成了牙膏,虽然事后,我多漱了好几遍口,满嘴还是怪味儿。我连包都放在车里不敢拿,我是爬楼梯上的10楼,很好,没有领导走楼梯,一路上鬼影都没见到。 回到办公室,门是开着的,但周东篱和炸两还不在,我立即松了一口气,即使是迟到,起码没被抓现行。见到周东篱桌上还有估计是哪个女生送的一块小点心,压着一张心形的小卡片,心中愤懑难当,二话不说就撕了塑料包装吃了。 又过了十来分钟,周东篱回来了,他看看桌子:“小刘,你有没有见过我桌子上有一块小东西?” 我头也不抬:“没见过。” 他拿着包装纸质问我:“你是不是吃了?” “我说没见过就是没见过”,我瞪大眼睛,“你也不想想多久没买好吃给我吃了,也不知道你怎么当领导的。” “那是监控室的阿霞送给我的……” 我更是气不打一出来:“就算天仙送的又能拿我怎么样,我就是吃了,你还能从我肚子里掏出来?” 这时,炸两也回来了:“你们又吵什么呢?” “我只是吃了他一块小点心。” “你吃的不是小点心,是牛奶味的手工皂。”周东篱戏谑地看着我。 炸两幸灾乐祸之余倒还有点担心:“行啊,依依,你真是我救命恩人,要是你不吃,说不定就是我顺手给拿去吃了。你,没事吧?” “怎么不早说?想害死我吗?” “你有给机会我说吗?”周东篱拧开一瓶矿泉水给我,“没事的,你多喝点水,把它兑成肥皂水就得了。肥皂水不但没有毒,吃了有毒的东西,还能喝肥皂水催吐呢。你,不会不知道吧?” 好啊,这一大早用洗面奶刷了牙还不算,还吃了块手工皂。 “还催吐呢?不用,去现场看看,保管什么都吐了”,走廊里有人匆匆跑过,“周队!北环路口现场,带你的人赶紧过去。” 三 北环路口人流车流并不算密集。绿化带边上的路灯是T型和F型的合体,也就是说路灯的高度分为两级,而低的一级大概离地2米多一点,而防水雨布包和鞋子原本就是被一根鞋带拴在一起,挂在低的一级路灯头上面的。 既然能折腾出让我们刑侦支队倾巢而出的大动静,防水雨布里面包裹的自然是人的头颅。但这颗头颅不简单,这是一颗湿漉漉黏糊糊有着黑色痂皮的头颅,应是受了某种矿酸(很可能是硫酸)的腐蚀,因而严重毁容,但隐约看得到五官应在的位置,而在它的嘴里还塞着什么,让这张嘴圈成了一个O型,呈现出了惊怖的表情。而和头颅几乎同时跌落的那只鞋子,是一只绑带的女式高跟鞋,很挑逗的夜店款,38码,对于女性来说,是大众化的尺码。只是那只鞋子就像被刻意杜绝了提取检材的可能性,因为它也被矿酸腐蚀过了。 “周队,这个人头,也是我去看吗?” “嗯,不然呢?” 我从兜里掏出橡胶手套,吹了两遍,确认没漏气,戴了两层,蹲了下去。 “这人肉都腐蚀了大半,还是挺好判。”我把人头提了起来掂了一下,“眉弓发达,眶上缘圆钝,前额倾斜,颧骨与颧弓也突出,应该是个男的。”我又仔细地抱着人头摸了一圈:“颅骨凹陷骨折,但我认为这不是致命伤。致命伤还是在脖子上……”我举起人头端详,发现颈部的肌肉及血管的断端有明显的收缩,很可能是切破静脉,令到颈静脉的负压吸入空气发生空气栓塞死亡。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肥皂剧里经常演的,别人在静脉输液,有人往导管里打了一针空气什么的,就是想引起静脉栓塞,不过一针管的空气当然是不够的。 “别卖关子了,赶快看看它嘴里塞着什么?” 我把那东西掏出来,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因为,那是一截阴茎,俗称JB(你们懂的)。JB的切口哆开,证明它是切下来的时候,主人还是活着的。此刻,它却要与一个毁容头颅的唇齿相依。 “操,刘依依,把我们全部搞ED了你负责呀!”炸两骂道。 “如果你们都ED了的话,我还能负责什么?” “赶紧塞回去。我是说恢复原状。”周东篱也对此不忍直视。 我不但没有将它塞回去,还凑近了看。 “这个色号是最近很火的人鱼色啊!” “什么人鱼?在哪里?” “是人鱼色,我找了很久,所有的海淘代购都买不到了,没想到在这里见着了。”我一边说一边用保存套管棉签刮了刮那截JB,收集检材。 再从头颅的切口处采集了一些组织,以作DNA检测。可是如果本身DNA库里没有收集该人的资料,也不可能查清楚尸源。我们甚至要搞清楚这个头颅和这根JB是不是同属于一个人。 “死亡多久了?” 我翻了翻头颅的眼皮:“应该不超12小时。” 这时,周东篱的手机又响了,他接完脸色凝重地说:“一个黑诊所里的医生被杀了。” “牛事未了,马事又来!”炸两叹道。 “炸两,你先把检材送检验中心,跟那谁说是小刘赶着要的。” “为什么要说是我?” “因为这是绿色通道”,周东篱吩咐其他兄弟把尸块处理好,便对我说:“反正等化验结果还需要时间,先到黑诊所看现场吧。” 四 这家黑诊所,开设在陋巷之中。与平日里所见的有着自己名称和在门口光明正大地悬挂着写着“卫生局监制”的红十字小灯箱的正规诊所相比,黑诊所自然是小家子气的,只有一个小小的招牌,上书“诊所”二字。 虽然现场已经拉上警戒带,但外围还围着不少群众。 “这是黑诊所啊,从来没注意到他们无证。” “死的好像是那个姓杨的医生,那杨医生就住在这……” “让一让,让一让,警察!”周东篱拉起警戒带,让我钻了过去,他随后跟了上来。 “这家诊所生意还是不错的。”周东篱一进诊所的门,就看见了门前靠墙摆放着一些木制条凳,由于坐得人多,木质也被打磨出油性的光泽。 “黑诊所怎么还会这么多人呢?” “什么病都能看,花钱少,而且就近。” 这间黑诊所只有两个接诊医生。一个姓涂,是个女人,中午12点到午夜12点;一个姓杨,是个男人,午夜12点到中午12点。涂医生的诊室靠门口,死者杨医生的诊室靠里面,两间诊室只是一墙之隔。杨医生的诊室要更宽敞些,因为他的诊室里还有一个里间,里面还有一张床,那就是杨医生休息的地方。 杨医生当晚估计已经在休息中了,因为他既没有穿着日常接诊的白大褂,也没有从墙壁上取下听诊器,他就这样左胸满是血,跌坐在诊室的墙角。 他的诊室资料被翻动过,桌子底下的保险箱也有被撬过的痕迹(但未能成功打开),钱包也不翼而飞。 我一边检查尸体一边说:“他左胸受了致命伤,是贯通伤,但这绝不是普通的枪弹伤。如果是的话,创缘会外翻,而且射出口会大于射入口,但这个射出口和射入口大小几乎一致。”我站起来看了看墙壁,发现一个小小的凹坑说:“这里有血迹,原本那个创造了贯通伤的东西就在这,被凶手抠走了。” 我查看了尸体的左腕,上面有一圈相对较白的皮肤,正是一个手表的影像:“应该还有一个手表。” 周东篱在诊室内四处走动。 他回来告诉我:“我没发现杨医生的手表,你还有什么发现?” 我难得敢下定论:“所以,这是一宗抢劫杀人案。” “错,这是一宗伪装成抢劫杀人案的谋杀案”,周东篱快步走到诊所门口说,“没错,凶手很冷静,他走的时候还灵机一动,把现场伪装成抢劫杀人,但门口写着‘休息中”,当时门自然是上锁了,可是门窗上均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所以这个凶手——” “凶手是病人!” “也可能是熟人。”周东篱补充说。 “再退一万步来讲,我刚才也去看了,诊所虽然是黑诊所,但里面还是有药房,里面多少有一些珍贵药材,都标注着药名,找来也是不难,可是那些药材一点都没少,凶手怎么会光把那杨医生的财物卷走了,不合理啊”,周东篱说,“绝对不是谋财。” 周东篱看了看杨医生尸体的位置,又模拟了一下:“看椅子的位置他起来的时候很匆忙,而且来不及将椅子扶正,这不像他的习惯——虽然他的诊室被翻动过,但一些抽屉都有条理都标记好了里面放置的物品,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会任由自己的椅子东歪西斜。”周东篱佯装在椅子上坐下:“但是,如果他坐下来,又匆忙之间站起来,甚至来不及扶一下椅子就往后躲,就会变成这样。他一定是坐下来,受了惊,然后站起来,往后躲——” “凶手拿出了凶器对准他,所以他站起来往后躲。”我疑惑地看着周东篱。 “不对,设想一下,如果凶手一进来就拿凶器指着你,你还敢做出这么大动作吗?他一开始肯定是坐了下来的。” 周东篱反复地念叨:“受惊,往后躲,对了!凶手一定说了什么,让杨医生受惊了。” 我在杨医生椅子前的桌子上,发现了一滴与众不同的血迹。 因为杨医生是心脏受了贯通伤,理应是以他为中心的喷射血迹,尖端是喷射方向而这滴血迹是圆形的,边缘光滑略带锯齿状,很明显是滴落的血迹。我用棉签把血迹提取了:“答案也许就在这里。” 五 回到局里不久,检验哥哥的电话就打到我的手机来,我循例是按下免提与周东篱一起听:“依依!周队在吗?” “我在。” “哎,依依你还是别听了,我直接跟周队说吧!” “你打到我手机来,叫我别听是啥意思?” “你说就行了,小刘有什么没见过。” “那谁刚才送来的检材,都检测过了,头颅跟JB是同属一个人,但DNA库里没有,对比不上。” “那就是还查不到尸源了。” “不过有个好消息!” “我说过了,杀人案里没什么好消息!” “哦哦,是有新的线索。不过你还是叫依依回避一下吧!” “行了,我让她回避了,你说吧。” “另外有一个检材,依依没有标明是在什么地方提取的,但是我用显微镜观察过,这种扁平的、多边形的细胞,应该是口腔上皮细胞,口腔上皮细胞呢,主要分布在口腔两侧颊部……” “你有完没完啊?说重点行不?” 这时一直不吭声的炸两插话了:“他的意思是说那JB曾被人口活了。” 周东篱不动声色:“有什么奇怪,本来就是插在那头颅嘴里的,大家不都看见了吗?” “什么?!也是从JB上提取的?”检测哥哥在电话里惊叫,“可这跟那颗头颅的DNA不一样呀!” “那么这口腔上皮细胞比对上什么了没有?”我听出了弦外之音,做活体DNA检测一般都爱提取口腔上皮细胞啊,我忘记我不该在听,插了话。 “咦?依依,你怎么还在?你听这些不好吧!” “她什么没看过?她没事还往草榴网写稿去呢。”炸两嗤之以鼻。 “根本没这回事。”我嘀咕。 “那你是不是承认过给女性情感期刊写那什么隐私小说?” “早十年。”我翻了一个大白眼。 “都扯哪里去了?到底比对上什么没有?” “有,一个女的,30来岁,有违法前科,早两年赌牌九被抓了,被采集入了DNA库。” “名字?” “王小葵。” 挂掉电话之后,周东篱扭头对炸两说:“对了,另外黑诊所杀人案的检材你也送一下,顺便把之前的检测报告都取回来。” “为什么又是我去啊?依依也闲着。” “检验中心那货对依依不怀好意,打着依依的旗号就行了,别让依依老去那。” 我看了看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danhuaa.com/jdhzp/7338.html
- 上一篇文章: 展开说说开一听去年今日的罐头
- 下一篇文章: 今天立夏北京人爱的这11碗面条儿您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