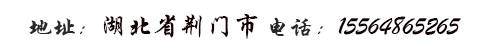看完之后,我想去一趟广州
|
跟着编号的镜头,阅读广州的十年变迁。 多久了,数一数,离开南方,到达北地,已经十年。整整十年,那些最有办法没办法的、盛放和狂妄的、无所畏惧和小心翼翼的生命时段,最灿烂的二十岁少年期,一来一回,南十年,北十年,连求饶的念头都还来不及萌生,就这样从豆荚子里爆裂,落地,生根,又渐次长成新的芽新的苗。再怎么样身处北方,干燥的鼻息里终归留着十年前的潮湿和粘稠,味蕾里也残留无法被改造的清淡喜好,再大的多环城市,离不开的念想里总有梅雨季湿滑的街道上,趿着拖鞋踢着水花的少年身影。念念不忘的结果是,至今我心依旧属于南方,依旧属于那个大半个少年期度过的广州。自认为后来写书出书,用文字造练的成长纪念册里,持续消耗过往的旧事和经历,都很难绕开那些年,那些时日。 一十年前,我带着大号的行李箱,一路寄运了数十个牛皮纸箱,离开广州迁移北京,把在广州曾经的十年生活,硬生生打包进了这些没有情感号召的纸皮箱里。从一个城市迁居到另外一个城市,对少时的我并不所谓,不畏离别也不畏新境,总认为的是有朋友的城市,就是适合的城市。三十岁之前,我的成长分别属于福州、潮汕和广州。7岁之前在福州,17岁之前在潮汕,27岁之前在广州。总归是离不开南国,绵而不绝的雨水、台风季、温热气候、潮湿空气、无数连名字都几乎叫不出来的海鲜,以及高颧骨黑皮肤的南方人、粤港流行曲里俗透了的情爱哲学,形成了我对南方的记忆。 大学期间,广州白云山脚的课室里,巨大客机每天在头顶轰隆隆地起飞和降落,不断掩盖了讲台上老师的声音。如今老白云机场早已成为记忆里不能回头的旧事,巨大的引擎声跟着旧年代的粤语流行曲、连同挨近的东方乐园,记忆里拆剩的摩天轮丁零肢骨,一并掉入不再启动的旧漩涡。那个片区,往后不经觉就变身大型体育馆和新型楼盘,旧校区也被而后新起的巨硕的集成式大学城所迁并。 那时候书是不好好读,混网络论坛,匿名写沾沾自喜的诗歌,画漫画,没日没夜地爱一个人,深夜窝在宿舍的上铺读石康的小说《晃晃悠悠》、《支离破碎》,以文字感应北方城市的彼端面目。北京这个城市对那时的我来说,就是另外一座山,居高而住的乌托邦放荡而骄傲的年轻人们,过着“晃晃悠悠”醉生梦死的超现实生活,欲望五光十色的,爱恨也峰高海远的。年少自是对事情是有向往的,向往乌托邦人,向往世界环游,向往做一个自由的野人,向往空气远处的灯红酒绿,向往小世界之外的山光水色。人都是那般,离开原来的城,抵达更大的城,轻易得到了,又犯着贱开始缅怀过往,过往必然都是在一寸寸失去,本该自然丧失的,却往往得不到善待,人总是倔强地往回奔往回奔,试图从记忆里捞取一笔什么,用以保全一点点薄凉的安全感。 如今总要说“回去,回去”,回去那座久离了十年的广州,而我总是进入催眠式的心境,试图认为其实自己并没有离开,或者没有离开多久。在北京长居,依旧吃广州的食物,煲广州的老汤,听着老派的粤语金曲,写着跟广州有关的故事。恍惚间,我似乎还住在那一年的龙津路,爬着没有电梯的旧楼层,冒着初夏的汗在瘦小的单人间里,隔着焊了铁网罩的窗台,望着楼下粥铺进出的西关人,望着对楼穿着汗衫暧昧不停的男女,望着南方的灰鸽飞过不那么蓝的天空,发出咕咕咕的叫声。 二 记得读民国作家倪锡英《广州》一书里,是这么描绘这座城市:“广州是一个全年和暖的地带,冬季没有堕指裂肤的寒风,也没有阶前盈尺的白雪,像永远拥在春天的怀里似的。每当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时候,就不禁使人联想起这个近热带的南国的都市来了。”没有寒风没有冰雪,多数时间暖煦雨水多,于是潮湿和粘稠,广州夏季长,冬季短,时不时身体就像蒸炉里的包子,稠汗在皮肤表层赖着不走,非要等到空调大开,才略显舒缓一些。觉得幸运,是因为移居北京之前,我能用对半的青春来体会广州,那些像独家剧目的影片里,一场场凡间民生戏,教会了一个反骨少年如何正面地进入一个城市,并不经觉地爱到骨里。 这场不长不短的戏目里,人们漫步在西关骑楼的檐底,盛夏的热度让人轻易湿了背,白而旧的恤衫依贴住皮肤,湿出一些氤氲的形状;荔湾步行街上茶楼食肆门庭若市,老广州人的一天,胃口从早茶点心开始直落到日暮,虾饺、烧麦、牛杂、凤爪轮番攻占肠胃;游客和本地人混杂的商业街上,卖“鸡公榄”的中年男人,身着艳色纸扎大公鸡,吹着唢呐叫卖身上的白榄,孩童们围着这公鸡人奔跑欢笑;狭小的长巷“状元坊”,挤满张狂傲气的青少年,忙着打耳钉、吃碗仔糕、买便宜的街头服装,与不同的学生仔接踵摩肩;建设六马路一拐弯,到达环市东路,再拐弯进入淘金路,路与路之间,留着旧居的往事历历在目;东山口红砖老洋房里,密集而居的本地人,每天开窗所见,除了长满苔藓的老墙,就是花气袭人的满树紫荆花;夜间的紫红色三角梅蔓延在人行天桥,三角梅自是没有什么香气,它甚至寻常得不被人在意和矜惜,但温黄的路灯下它就是静静开放,如此普通而沉静的美感;天气热的时候,退了休的老人干脆摆起麻将桌在街口,哗哗地洗着牌,聊着街坊琐事,嘴里碎碎的粤语尾音拉得长长;雨天来了,逛街的人儿也无所畏惧,躲在骑楼之下,一路照样逛下去,从商铺林立的上九路逛到食厮聚集的第十甫,从繁华年轻的北京路逛到文具和干货混杂的一德路;然后再从省图书馆淘一本书出来,走入文明路另一侧的糖水铺,玫瑰甜品是不二之选,借热腾腾的凤凰蛋奶糊来暖一暖胃…… 我也自是没有机会目染欧阳山《三家巷》小说里的广州,那布满熟透荔枝的、“像无数千、无数万颗鲜红宝石浸在水中一样”的弯弯曲曲的荔枝湾水道,但也被这十年的幻变,更改了初始的记忆——旧时往往只闻荔枝湾,未曾目睹过其历史里曾有的盛况,因为自年,随着逢源桥水道的被覆盖,荔湾涌成为被掩埋的过往;如今那新生的、故道复建的荔枝湾,也已不是那十年间,我对其“只闻其名不见其踪”的旧印象,遗产也从历史里回归到现实。 那些旧年的戏份跟着时代走远了,恍然十年,离开的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段,还有滚落悬崖的过往。如今却是状元坊不再,鸡公榄不再,急景流年,荔枝湾重现,而绿地盎然的冼村,也平地而起焕然成一座崭新的城,叫“珠江新城”。年前后,我拍下只有一栋孤零的仿欧建筑的珠江新城,那时谁知道时间会如此迅猛地篡改了记忆。 不变的,大抵只有那亚热带暖暖的空气。这空气着肤的触感,是一念。 三 大学毕业之后在杂志社工作,负责内容编写,写新兴流行和生活方式之事,也写诸如怀旧香港和老式广州的沉淀记事,后者因为往往需要深度挖掘几近被当代城市人所忘怀的老事旧物,跟着资深编辑在广州游走,从西关到东山,从白云到海珠。 记得那时读到最爱书写广州的作家“黄爱东西”的书,从书里学会她对广州的一个私人词汇:“花事”,大抵就是写了各式各样广州的花,从鸡蛋花到栀子花,从米兰花到姜花,以气味来辨别这个城市的特有属性。搬离广州前,住在东山口,庙前西街,路两旁是老式红砖和改造的瓷砖墙面参差相并的老洋房,廉价的外贸服装店隐匿在街的一侧,有友人住在老洋楼其中一单元,有次上门前去喝酒开趴,大白天的,推开阳台门,满眼的紫荆袭来。后来回想起,才觉得那大概就是所谓广州的花事。气味是一种,而广州味道,更是这个城市给人所带来的最单刀直入的生理侵略,当然,这种侵略是建立在美好的味蕾之上,而你心甘情愿,乐在其中。黄爱东西同样爱写广州味道,写吃,在《广州女人》里她是这么说:“如果你们中间少了那张饭桌,少了茶楼食肆那种轰轰烈烈的人声和排山倒海的场面,那么广州人对你的那种满腔的热情和爱心,真是不知如何表达才好。” 于是从南信的双皮奶和牛三星,到趣香饼家的鸡仔饼和蝴蝶酥,从欧成记的云吞面,到顺记冰室的鲜椰子和香芒雪糕,从陶陶居的正餐和广州酒家的夜茶,到龙津东的葱油鸡。还有芝士虾包、蟹子云吞、红绿豆沙、红烧乳鸽、霸王花猪肺汤、古法叉烧、布拉肠和姜撞奶……只要一在这城市停留,这些口腹之欲都统统得到满足,却也不会想要列个清单,列给行将远离的自己,列给十年养成的味觉。因为总觉得,那些年的旧时光自己仍有气力负得起,回来,吃一吃,就开怀。这地道的美食,林林总总在舌根留着不灭,又是一念。 四 时至今日,都离开了十年,还是有些关于地名的念想未能解开。离开前那两三年住东山口,被周边的地名迷住,是打心眼里的喜欢,觉得诗意,像读沉甸甸的古本歌赋:恤孤院路、烟墩路、永胜上沙,好听到会一直惦念,每次回去,都要走走。至于那条寺贝通津,后来总算是理了清楚含义:“津”在旧时是码头之意,“寺”意指旧时原有一座东山寺,“贝”音通“背”,寺贝通津就是指东山寺背后通往海边码头的一条路。东山寺早已卷入历史不知去处,曾经有寺的东山口,关于寺贝通津的这个路名着着实实留了下来,却也为后人留了一道诗意的谜。 以往散步东山口片区的方式,都是庙前直街往东,拐进恤孤院路或培正路之前,吃一份仁信双皮奶,加莲子或红豆,纯粹依据当时口舌的意愿。恤孤院路和培正路都一般清净,偶有上下课的学生结伴奔走,路边的老洋房有的被粉刷成尴尬的面貌。一路走,路过中共三大旧址时顺道去逵园画廊看看展览,会会老友。不知不觉就会走到新河浦,河涌边常有夜来花香,一路的临街小店零星被改成私房菜、设计小店和小型画廊。最后穿过龟岗大马路后回到东山口起点,便算是步行了一圈完整的东山口片区,时间不匆促的话,还会往庙前西街绕一绕,窥一眼曾经住过的小矮楼,更多的是为了路过街角楼前那棵不败的古榕,会一会树荫下拉家常的老居民们。 大概最动听的路名,统统都集中在了广州。往西,更不用说光孝路,诗书路,晴澜路,渔唱街、怀远驿……每一个像是诗词里撷取出来的字眼组构成的路名,或多或少都有其深远的来由。市井气的街道,与诗般的路名,大概是我离别广州之后的又一念。前阵子从上下九拐弯走入清平路,横越过六二三路进入沙面,想起倪锡英的《广州》一书里,说这片曾是英法租借地的沙面,与毗邻的西堤码头比起来,“静谧得像世外桃源”。曾经我在沙面某个老楼里工作过半年的时光已去,如今也已绝不敢轻易称沙面为世外桃源,节假日里,这里人山人海,往日静谧的道路变得几乎水泄不通。当时走在沙面,就觉得记忆那么的疏离,场面又那么的亲近,似乎十年真的没有多远。 关于作者:编号摄影师、作家,生于广东,现居北京。城市美学私享者,以摄影、旅行、写作和自出版作为生活创作四件套,长期对焦新生代流行文化和生活状态,探求当代中国新青年的爱与性及性别。已出版旅行小说摄影文集《除非我们虚构了爱》,摄影作品集《No.》、HiddenTrack,旅行文集《漂游放荡》。 编号的新作 除非我们虚构了爱 编号 电子书价格:¥20.33 2个秘密×一封晚安书×多张编号摄影作品。如烟缥缈的爱与性的镜头文字,现实与虚构、偶然与无序交织的故事,充满张力与故事感的大量胶片图片,游走在禁忌和天真之间,真实坦率直指人心,无论感动还是惊讶都足够落泪深思。 *实际价格以亚马逊北京白癜风手术需要多少钱北京中科医院是骗子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feizhouxiangdx.com/jdhzp/122.html
- 上一篇文章: 鸡蛋花为什么不结鸡蛋果
- 下一篇文章: 教你认识全世界所有的花,认花不求人不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