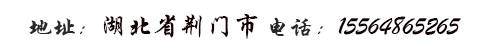我爱你,是一生一世,是至死不渝
|
摄影:overwater模特:七帆 1 颂白还记得自己十七岁时候的样子。 那时她很瘦,肩胛骨将衣服高高地撑起,显出蝴蝶似的痕迹。有小姑娘羡慕她,问她怎么减的肥,她只觉得那人脑子有病,把人一推就走了。所以那时她人缘也不行,班上总有风言风语,说她是小太妹,在学校外面认了大哥,每周四不参加晚自习是为了去打群架。 这流言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一旁的冯嵇笑得喘不过气来:“那你周四为什么不参加晚自习呢?” “你是猪吗?我去挨打啊!” 她说得有点大声,从旁边路过的同学看过来。她瞪回去,把别人吓得慌慌张张跑了,冯嵇又哈哈大笑,对着她伸出手说:“拉我一把,我笑得都爬不起来了。” 颂白一脚把他踹倒,他习以为常地一个骨碌站起来,跟她好兄弟似的勾肩搭背:“你改改说话的臭毛病吧。去针灸能被你说成挨打,我是真不意外有人传你的八卦了。” 她把冯嵇的手给甩开:“谁在乎他们说什么。” “话不是这样说,万一你以后功成名就,这可就是你的黑历史。” 她越发不屑:“我都功成名就了,还会怕黑历史?” 她那时说得坦荡漂亮,可后来才知道,原来不是每个人长大了都会变成厉害的大人,想活得体面就已经很难。冯嵇担心她会被找到黑历史简直是杞人忧天,她泯然众人,变成了一点都不特别的成年人。 所以当她重新变成十七岁时,她站在镜子前看了很久。 她还是那样瘦,只是高中生天天熬夜学习,眼下带着黑眼圈,好在年纪轻,皮肤底子好,摸上去满满的胶原蛋白。 这就是年轻的滋味,她看得出了神,冷不防外面有人喊她:“虞颂白——” 她愣了一下,把窗子推开,果然看到冯嵇站在外面。他个子高,可是穿衣服吊儿郎当的,校服拉链只拉了一点,露出里面的限量版球衣。虞颂白看他,他也抬起头看她:“还不下来,上学要迟到了!” 她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看了一眼客厅的挂历,这是个周六,高三生还要补课。妈妈正在拖地,看她还不走,催促道:“磨蹭什么呢?人家小冯都等你半天了。” 她“哦”了一声要走,妈妈又把两罐牛奶塞给她:“丢三落四。” 她下了楼,冯嵇已经迎上来,很自然地从她手里把牛奶接过去,插上吸管后又递给她。她下意识地问:“干吗?” “大小姐,你不是不喜欢插吸管吗?” 她不记得自己有这么矫情的习惯,十有八九是冯嵇给惯出来。两个人并排走,冯嵇不老实,走着走着突然跳起来做了个投篮的姿势。她看他一眼,他也才十七岁,有两道浓密的眉毛和一双漂亮的眼睛。她含糊地想起来,初中、高中,他好像一直是校草。 只有小孩子才会这么幼稚,评选什么班花、校草的。她忍不住抨击他:“耍什么帅?” “这不叫耍帅。”他一本正经地反驳,“我只是展示我的帅,懂吗?” 她听了,觉得他居然有点可爱:“懂了。” 他却突然站定,她奇怪地看他一眼:“又怎么了?”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说,“你居然没揍我?” 她翻了个白眼,冯嵇又过来说:“今天有随堂测,记得给我传听力答案。” “高考是为了自己,你糊弄老师还是糊弄自己呢。” 冯嵇这次是真的惊呆了:“你是不是发烧了?” 她这才想起来,自己不是二十七岁,而是十七岁。可话已经说出去了,她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这一天,冯嵇一直用探究的目光看她。她怕被他看出破绽,放学后两个人一起回家时,他终于开口:“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她提心吊胆,就听到他说:“你是不是为了和三班那个臭小子考同一所大学,才会突然这么用功的?我劝你死心吧,他的目标是北大,即使你投胎转世再学十年也考不上。” 三班的臭小子是谁她早就不记得了,傻愣愣地看着冯嵇,听他冷酷地威胁自己说:“还有半年就高考了。虞颂白,你要是敢早恋的话……” 她问:“你就怎么样?” 他思考了半晌才说:“我就告诉你妈!” 她实在忍不住,笑得站都站不稳,只能扶着他的肩膀,他有些不自在:“笑屁啊,我说真的。” “冯嵇,我怎么过去没发现你这么可爱?” 她说着捏了捏他的脸,他却像是被烫到,立刻跳出去好远。借着路灯,她看到他的脸通红:“你……你简直不可理喻!” 他说完转头就跑,她笑了半天,却又有些怅然。可那边街角,冯嵇臭着脸又走回来。她有些意外:“你怎么又回来了?” “废话。”他说,“我不送你回去,这么晚了,你一个女生怎么走?” 他呀……这一瞬间,心柔软成一湖水,千丝万缕,系着人间的星同前生的梦。她望着他许久,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2 颂白和冯嵇算是青梅竹马。 两个人是同一年出生,颂白比冯嵇大三个月,后来上了学,两个人还是一个班。冯嵇从小就长得乖巧漂亮,老师喜欢他,让他当了班长。放学排队出去,他帮老师维持秩序,突然对颂白说:“你出列。” 颂白那时候还是个乖孩子,老老实实地出来,他又指挥她站在自己身边。颂白小声问他:“为什么叫我出来?” 他板着脸说:“你别问。” 颂白吓了一跳,以为这是什么大机密。等往外走的时候,老师要小朋友们手拉着手免得走丢了,他握住她的手,很小声地说:“咱们站一起,就可以手牵手出去了。” 他说完,又一本正经地目视前方。音乐委员起了调子,大家一起唱着队歌往外走。可她总记得,他假装正直,其实那么小就会耍花招来牵她的手。 他们俩一直都在同一所学校,九年义务教育,两个人就在一起九年,放了学总是一起回家。 后来学校就有了风言风语,说他们俩早恋。他们上的是重点中学,老师管得严,颂白脸皮薄,放了学不等他一起,就自己先走,他则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 橙红色的日光落下去,在柏油马路上拉出长而深的影子。男孩总是发育慢一点,都已经上初中了,他才猛地长高,校服袖子短了半截,被他满不在乎地撸到小肘上方。 周围都是人,她骑车有些费力,索性下来推着走。他不下车,仗着腿长,就那么脚点着地滑到她身边:“你跑那么快干吗?” 她不说话,他“嘿”了一声:“这是要和我划清界限?” “没有。”她总算开了口,“我妈让我放了学早点回家。” “拉倒吧。”他嗤之以鼻,“虞颂白,你就是怕了。” “我怕什么了?” “你怕老师批评你,你怕别人传你谣言,所以你就把我给抛弃了,对不对?” 他说对了,可她不能认,似乎承认了就是告诉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胆小怕事的坏人。她低着头不说话,后面有人冲他们俩摁喇叭:“走不走了?” 他转头对着那个人吼:“催什么!给我老实等着!” 这么一吼,没人催他们了,大家的视线投过来,颂白越发坐立不安。她上了车要跑,可他跟在后面,让她甩不脱。等到了人少的地方,他一个超车过去,把她给逼到角落里停下:“你给我说清楚。” “有什么好说的?” “你以后是不是都不理我了?” 她抿着唇,看天看地就是不肯看他。他没什么耐心,几乎是有些气急败坏地等着。她到底说:“我没有不理你。” “那你是什么意思?!” 他的声音大了点,像是在吼她。颂白没忍住,从眼睛里滚落两颗泪珠。这两颗泪珠把两个人都吓到了,他夸张地往后退了一步,把声音压得很轻缓地说:“你……你怎么哭了?” 她哽咽道:“你拿我发什么脾气!”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连忙赔礼道歉,“错了错了,我就是怕你以后不理我了。” 可他不知道,哄女生不能这样。他越说,颂白哭得越厉害。他围着她团团转,像一条殷勤的大狼狗。半晌,她才抽抽搭搭地说:“我……我就是不想被人……说我早恋了。” 他松了一口气:“谁说咱们早恋了,咱们这不是纯粹的革命友情吗?” 她掐他:“谁和你革命友情了!” “是纯粹的姐弟情谊。”他连忙改口,“颂白姐,我的好姐姐,别掐了,都掐破皮了。” 他挤眉弄眼,她“扑哧”一声笑出来,眼泪还缀在睫毛上,可嘴角已经迫不及待地勾起来。那天之后,班上就没人传他们俩的八卦了。期末考试结束,两个人稳稳当当地排在年级前五,早恋这回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颂白问他,他说得轻描淡写:“我找那几个大嘴巴的人聊了聊。” 怎么聊的颂白不知道,可她说的话,一字一句他都认认真真地放在心上。她说不想被人说闲话,初中三年就再也没听到过关于自己的流言蜚语。等升上高中,遇到初中同学,那个人还心有余悸:“我们哪敢说啊,都怕挨揍。” 她有些意外:“他还会打人?” “没有,但他看起来真的好凶。” 在她面前,他永远驯顺乖巧,哪怕已经长成高大英俊的少年,可仍旧愿意弯下腰来让她摸一摸头。 颂白那个时候有所猜测,却没有问出口来。 她以为光阴似箭只在课本上,少年人的时间永远漫长,未来永远光明。她以为自己和冯嵇可以永远这样快乐,可以永远……在一起。 3 颂白发现自己生病是在上高二的时候。 体育课时她突然晕倒了,医院检查后发现是心脏出了问题。她没当回事儿,回去学校后有人问她,她就敷衍说:“贫血。” “一定是你太瘦了。”那个人不懂装懂,“你不知道,你当时一晕倒,冯嵇简直要疯了,抱着你就往校医室跑,我们都没追得上。” 她个子高,就算再瘦,抱起来骨头也是沉的。她“哦”了一声,那个人又感叹说:“你们这兄妹情,真是绝了。” 颂白总算问:“什么兄妹情?” “冯嵇说的,他说你们俩一起长大,他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看。” 颂白觉得有点不高兴,却又说不清是为什么,还是冯嵇先发现:“大小姐,谁又惹你不开心了?” 她不说话,他就跟在后面,老老实实地替她拎着书包。半晌,她才说:“你跟他们说你把我当妹妹看?” “那个啊……”他慢吞吞地说,“不是怕他们又传你的八卦嘛。” 颂白却说:“我看是你怕影响你自己的形象吧。” 他长得好,小迷妹很多,走在校园里总有人指指点点。少年人虚荣心作祟,被人喜欢不是不骄傲,可她不开心是更大的事情,他连忙解释:“真没有!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再说了,要是被我妈知道我在学校拈花惹草,不把我的腿打断啊?” 他母亲是书香门第,从小对他要求就严格,连她也受累,两个人总是一起站在窗台下背书。颂白信了他的话,抬脚踢了他一下:“你还敢说我是你妹妹?冯嵇,你狗胆包天!” 他咳了两声:“姑奶奶,给我留点面子。” 颂白忍不住笑了,视线划过路边的烤鱿鱼。可他这次铁面无私,揽着她的肩膀把她给掉转了一个方向:“你妈说了,以后不准你吃垃圾食品。” “又不是什么大毛病,搞得这么严格……” “虞颂白,”他却一脸严肃,“想吃,你得过了我这关。” 他手长脚长,把她夹在胳膊下面,她挣扎半天,终于宣告投降。在那之后,他对她盯梢更严,两个人必须同进同出,免得她嘴馋偷腥。每周四,她都会被送去做针灸。她不怎么怕疼,银针扎了满背,还在那里按手机指示他给自己带一杯奶茶过来。 门没关好,他直接推开进来,只看了一眼就立刻出去了。隔着屏风,她问:“让你买奶茶,没买错吧?” 他不知怎么了,慢半拍才说:“四季春半糖去冰,我怎么会买错?” “那你进来呀?” 他不说话了,还是老大夫笑起来:“小姑娘,你衣服没穿好。我看小帅哥脸都红透了。” 不说还好,一说外面的门就被推开又关上。是他落荒而逃了,可她趴在那里,脸也红了。之后她就不准他跟着一起来,一周七天,只有这一天他不用送她回家。 她的病说起来只发作了那么一次,除她以外的人都提心吊胆,可她自己不大当回事儿,体育课上还和同学一起打排球。还没到夏天,天已经很热了,树上的知了叫得很大声,她突然被人扯住手给拽了出去——是冯嵇。 他阴沉着脸,看着像是随时要爆炸。她有点心虚,小声问他:“怎么了?” 他没说话,先把她拽到树荫下的长椅边,把她按坐下,又给她递了瓶水。她喝了,他又递了条毛巾过来:“擦擦汗。” “冯嵇,”她受不了,率先投降,“我错了,我不该和他们一起打排球的。” 他问:“错哪儿了?” “我不能进行剧烈运动,我知错犯错,罪加一等。” “颂白,”他的脸色没那么糟了,在她身边坐下,长长地叹了口气,“我不是要管着你。可你妈叮嘱我了,一定要看好你。我真怕……” 怕什么他没说出来,把头仰在靠背上,一眨不眨地望着天。那天有火烧云,天空的颜色十分漂亮,映在他的眼睛里,像是琉璃灯花。她看着他,小声保证:“我以后会注意的。” “不注意也没事。”他却说,“有我看着你,你想出事都难。” 她叫了一声:“万一呢?” “不会有万一。”他很固执地说,“什么事都不会有。虞颂白,你一定会好好的。” 4 他是金口玉言,说她不会有事,她就真的顺顺利利,看起来也健健康康。她的十七岁平淡无奇,为了高考而努力,就算是二十七岁的她突然回来,也只能每天好好学习。 那年夏天比往年热得都要快,学校给高三生放了半个月假,颂白乖乖待在家里复习。头顶的吊扇转着,窗外的老桐树那么高,树叶遮出大片阴凉,下面有人喊她:“虞颂白——” 她看一眼,又把头缩回来。他也不气馁,自己踩着楼梯跑上来。妈妈在外面替他开了门,热情地把他引进来,又过来骂她说:“小冯来了你怎么也不理人?” 她叼着笔,歪了歪脑袋:“他又不是什么贵客,还要夹道欢迎?” 妈妈过来敲她一下,她吃痛,看他在一旁眉开眼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等妈妈出去,他立刻卸下好孩子的样子,歪三倒四地躺到她的床上:“累死我了。” “你干什么,马上就要高考了还乱跑。” 他“啧”一声:“我闭着眼睛,还以为是我妈在我面前念叨呢。” 她也觉得自己是有点老气横秋,咳了一声假装没听到。他却摊开手,掌心里躺着小小一个锦囊:“喏,今天早上特意上山求来的。” “什么?” “保佑你高考顺利的符啊。” “我闭着眼睛,还以为是我妈在我面前搞这种封建迷信呢。”她立刻反唇相讥,他却笑了:“颂白,你真是小肚鸡肠。” 女人总是这样斤斤计较,她喜滋滋地把符接过来,想了想,翻出一根铂金链子挂上,对着镜子试了试:“怎么样?” 他认真地端详片刻才给出评断:“你皮肤白,戴什么都好看。” 他说话语气平淡,越发显得真诚。她越发开心,他就说:“我替你扣上。” 链子很细,小小的扣眼要凑很近才能看清。她低着头,将头发全撩到胸口。他站在后面,个子太高了,只好弯下腰来。这一下,两个人就挨得很近,他的呼吸似乎吞吐过来,像春天四月的风,吹得满山花都开了。她忍不住动了一下,他的手就歪了歪,轻描淡写地说:“别乱动。” 她实在是紧张,说不上为什么,只好东拉西扯:“你打算报哪所大学?” “还没想好。” “只剩几天了,还没想好呢。” 他笑出声:“不是在等有个小气鬼来决定嘛。” 她假装听不懂:“谁是小气鬼?” “好了,系上了。”他把头凑过来,下巴几乎压在她的肩上,引着她看镜子说,“是不是有点歪?” 她忍不住去看他,镜子里,两个人四目相对。她脸颊泛着红,像是被霞光染的,又像是少女心神不属泄露的秘密。他又笑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悠然地直起身说:“只有笨蛋才会问‘谁是小气鬼’。虞颂白,你是猪吗?” 她张牙舞爪要揍他,两个人追逐打闹到客厅,被妈妈扣下吃饭。两个人坐一起还不老实,饭桌下你来我往踢成一团,妈妈被吵得没办法:“不吃就滚下去!” 他们从善如流地“滚”下桌,两个人明明就住同一个小区,她还要送他回去。路边的花开了,她说是鸡蛋花,他非纠正说叫广玉兰。她生了气不理他,他就捡了一朵,擦干净后递给她说:“小气鬼,给。” 她总算笑了:“闹了半天小气鬼是说我啊。冯嵇,你原来这么听我的话。我说让你报哪所大学,你就报哪所大学吗?” 她是玩笑话,可说出来后两个人都安静下来。那花捻在手里,瓣是绉纱似的柔软,她轻轻地拿指尖拈了,只在想他会不会误会了。 误会什么她没想好,还好他只是说:“是啊,咱们可是神雕侠侣,注定可是要一起浪迹江湖的。” “去你的。”她笑着说,却又有些伤心,“我可不当小龙女,一个人孤零零地活了十六年。” 他察觉到了:“怎么了?说着说着就不开心了。” “没什么,冯嵇,你可答应我了,咱们要上同一所大学的。” “我答应你的什么时候有过假?” 他说的是实话,可她却越发难过,只是忍着,生怕他看出来:“那谁知道呢?越好看的男人越会骗人,你要是敢骗我,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5 人这一生,一辈子有多长? 书上说,沧海桑田、海枯石烂,可人心多变、朝令夕改,这一刻的爱人未必下一刻仍视若珍宝。颂白后来读书看报,看那些爱情故事,男人对女人说出我爱你,故事就此定格,一切停留在高潮处,便再也不会变迁。 那一年的高考作文是半命题作文,颂白胡乱写了,出了考场,脑子还在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她和冯嵇没分到一个考场,最后一场考完,父母接她回家,妈妈忽然问:“你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发烧了?” 她随手摸了摸,只说:“大概是考场里太热了。” 其实天上有积雨云,沉甸甸地压在那里,似乎马上就要落下来。晚上冯嵇来找她,她没出去,听到妈妈在门外和他说:“一回来就睡了,大概是太累了。” 他有些担心:“不会是生病了吧?” “替她测了体温,没有发烧。” 他这才放下心来,半晌,门被打开,妈妈走进来,很无奈地说:“和小冯闹别扭了?” 她摇了头,妈妈又说:“他给你买了荔枝。” 荔枝都被洗干净了,拿冰冷着。她剥了一颗,咬一口,透心的甜。他总这样,面面俱到,细心得不像是这个年纪的男孩。可她记得,他小时候其实也会粗心大意,夏天带着她去游泳,她脚抽筋,差点被淹死。他被爸爸打个半死的时候没哭,去医院看她的时候却哭成个泪人。 “颂白,”那时小小的他抓着她的手抹眼泪,“我以后一定好好保护你。” 他对她好,养成了习惯就刻在了骨子里。他把她养成一个娇生惯养、坏脾气的小气鬼,他要她这一生都离不开他,想着他,也记着他。他是蓄谋已久的猎手,在她身上从未失手……她不敢再想,抱着被子蜷成一团。 那几天的梦都是乱的,梦里她总在哭,天永远在下雨,远方的地平线垂入深井,到处都是白的。她躺在病床上,麻醉药药效刚过,努力睁开眼看了一圈,只是问:“冯嵇呢?” 没有人回答她,他们哄着她睡去。她胸口三寸却疼得铮铮作响,像是有谁拿着一把小小的匕首在磋磨。她以为自己要死了,不知道是在梦里,还是在接下来的一生。可她终究醒了过来,手机不知疲倦地响着,她勉强接了,听那边的冯嵇对她鄙夷地说:“这都几点了,怎么还在睡?” 她觉得额角一跳一跳地疼,语气很差地说:“关你屁事。” “还有起床气呢。”他笑了一声,却又关心她,“嗓子怎么哑了?” “吃荔枝上火了。” 他连忙说:“你不会一口气吃完了吧?颂白,你可真是一只小猪啊。” 他这么说话,她就一点脾气也没有了,舍不得再对他横眉冷对,只好含糊地问:“到底什么事?” “今天晚上同学聚会……”他说到一半又收回去,“不然算了,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他是听出来她不舒服,才故意这么说的。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他:“你说,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能改变吗?” “你听过‘祖母悖论’吗?一个人不可能回到过去,在父亲出生前杀死自己的祖母,因为这样的话,他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没有例外吗?” 他笑起来:“怎么突然跟我讨论这个?这两天不会熬夜看科幻小说了吧?” 她也笑出声:“就是忽然想起来了。难得一次同学聚会,记得来接我。” 他还没回答,她就把电话挂断了。在他面前,她好像永远都这样不讲道理。晚上他准时来了,为了接她,还开了家里的车。她站在窗口往下看,他垂着眼睑不知道在想什么,后背厢影影绰绰的,像是放了什么——她知道,那是一大束玫瑰,本来被他放在后座上,在她下去之前又塞进了后备厢。 妈妈在外面催她说:“赶紧下去,总让小冯等。” 她问:“妈,我总让他等吗?” “小冯天天站在咱们楼下,邻居还问我是不是你请的保安。” 她忍不住笑了,却又替他感到心酸。下去时她走得很快,楼道里的感应灯应声而亮。他恰好抬起头,看到她,眼睛亮了亮,却又故意说:“这么刺眼,还以为是夸父逐日成功了呢。” 她“呸”一声:“是我的美貌把你给亮瞎了吧。” “差一点儿。”他一本正经说,“谢虞公主高抬贵手,我要是真瞎了,以后就看不到这样美丽的你了。” 她向他伸手:“那我的水晶鞋呢?” 他故意上下翻找:“哎呀,忘带了。” 两个人哈哈大笑,到了地方,又一直坐在一起。有人打趣说:“知道你们恩爱,可是也不用寸步不离吧?” 冯嵇怕她生气,刚要说话,她却说:“这叫捍卫主权,寸土不让。” 那个人识趣,不再打扰他们。她一转头,看他一眨不眨地望着自己。她哼一声:“干吗?” “你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嘿。”他像是要笑,又要忍住,犹犹豫豫的,就露出个傻兮兮的表情,“虞颂白,你真是嘴硬。” 她不理他,他还要问,被她拍了一巴掌:“老实点。” 他委委屈屈地应了,过了一会儿起身要去厕所,她也跟着,他这次有了意见:“这就不用一起了吧?” 她也觉得不合适,却仍坚持:“送你一程。” 她送他到厕所门口,实在不好意思,只好转身往一旁的天台走。天台上到处都是绿植,偶尔一颗开了花,小小的,白白的,却香气凛然。她蹲下去闻了闻,看到那边冯嵇走了进来,像是要找她。她没出声,果然,他身后又冒出来个女孩。她眯着眼睛看,把这张面孔和记忆里的脸对应起来,总算想起好像是六班的学习委员。 女孩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红晕,有种青涩的可爱。她耐心地听,听女孩向他告白。这样的好事情,他却一脸为难地东张西望,恨不得抓耳挠腮。女孩总算说完了告白的话,她也站了起来。他一眼看到她,像是看到了救星:“颂白!” 她走过去,站在他身边,面不改色地看着女孩。女孩的脸由红转白,像是要哭了:“你怎么在这儿?” “等我家冯嵇啊。”她淡淡地道,“他出门上厕所,我怕他迷了路。你们说什么呢?” “没什么。”冯嵇连忙说,又大呼小叫,“你胳膊上怎么起了个大包?” “被蚊子咬的。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非在这儿喂蚊子。” 她说着,拽着他的胳膊就往外走。他亦步亦趋地乖乖跟上,身后的女孩不知是不是哭了。这个她可管不着,因为一进拐角他就把她给揽住,一只手撑在墙上,将她困在自己和墙壁中间。 她没说话,他也没说,半晌,才带着点儿兴奋地问:“‘我家冯嵇’?” 她还是不说话,可他管不了,就像是看到骨头的大狗,欣喜若狂到了极点:“我说你今晚怎么看我这么严呢,就是防着这个吧?” 她总算开了口:“对。” “虞颂白,你说你……”他大概想捶胸顿足,还好忍住了,“你是不是吃醋了?” “是。” 他一下卡了壳,她望着他,知道是指望不上他了,于是扯着他的领子让他低下头来。他还带着喜从天降的僵硬,却顺服至极,唇与唇贴在一起的时候,就像这一生都过去了。她耳中如同听到雷鸣浪涛。 良久,久到他们几乎都要窒息,两个人才终于分开。他轻轻地拿手指替她把眼泪擦了,很温柔地说:“颂白,别哭呀。” 她原本不爱哭的,在他面前,这一生似乎也没哭过几次。可后来她变成个爱哭鬼,午夜梦回,将自己哭得几近昏迷。他是她的良药,可她却失去了他。 “说起来不好意思,本来应该我先说的,可是被你抢先一步了。”他有些不好意思,“我把花藏在后备厢了,打算回去的时候向你告白。颂白,其实我……” “你先别说。”她却制止了他,“在你开口以前,我想先跟你说件事儿。” 6 颂白和冯嵇吵得最凶的一次,是在高考结束后的暑假的同学会上。 那天她没怎么打扮,穿着短裤和T恤就去了。路上堵车,她到的时候,聚会已经开始了很久。冯嵇不在那里,她那个时候脸皮薄,没好意思问,还是有人看她一直在张望,才过来跟她说:“冯嵇好像去天台了。” 她只说:“去那么久,喂蚊子吗?” 那个人又说:“好像六班那个学习委员也跟着他一起去了。” 六班那个学习委员,这个称呼很疏远。同班同学总是天然的伙伴,是要同仇敌忾的。她心里“咯噔”一声,犹豫了半晌才往天台走。那天的天台上也放了很多绿植,隐隐约约的花香飘过来,倒有种粗糙的罗曼蒂克的感觉。她看到冯嵇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到了极点。而他面前,有个女孩正踮着脚亲吻他的唇。 多浪漫的一幕,多狗血的一幕。 她转身,没看到冯嵇将人推开的画面。她逃跑了,也就错过了冯嵇后备厢里的那一大束玫瑰。回家以后她就病倒了,这一场病来势汹汹,医院。等她再睁开眼时,才知道,冯嵇已经不在了。 “你是被人在小巷子里发现的,警察调了监控,看到有人拦路抢劫,和你发生了肢体冲突,劫匪情急之下拿刀捅了你……下着雨,夜又深,等你被人发现医院的时候,已经迟了。” 颂白靠在栏杆上,望着天空,轻声说。她身边,冯嵇认真地听着,半晌才问她:“然后呢?” 医院的时候还能开口,医生问他有什么话要留下。他想也没想,很费力地说:“把我的心……给颂白。” 那是他留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句话,之后他便陷入半昏迷状态。医院之前停止了呼吸。医生将他的遗嘱告知了家人,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同颂白进行匹配。匹配结果成功了,她在二十六个小时后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 从此,这个世上没有了冯嵇,唯独他的心脏,仍在她的胸膛里跳动。 “术后排斥反应很轻,所有医生都说是他们见过匹配最成功的。我从麻醉中清醒后,一直在问你去了哪儿,他们不肯告诉我,所以我连你的葬礼都没有去参加。 “后来,他们瞒不下去了,因为你不可能会那么久都不来看我。我大闹了一场,他们才告诉我,你已经不在了……我以为他们是骗我的,直到他们带我去了陵园。你的墓碑上贴着照片,上面清清楚楚刻了你的名字…… “我妈说,你的钱包里其实没放多少钱,只是有一个小香包,打开以后才知道,那是你特意上山为我求的。求我一生平安健康,无病无灾。” “你好傻,都这么大的人了,还搞封建迷信。一个香包没有了还能再求,可你没有了,让我去哪里找?”她嘴角勾着,可眼泪顺着脸颊慢慢地滚下去,“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 他猛地将她抱入怀中,她无声地哭着,浑身颤抖,却毫无声息。她也像是在这一场描述中死去了,死在没有他的岁月里。 “我那个时候也不想活了,是你妈妈骂醒了我。她说你的心脏在我的身体里,我要为了你好好活下去。我高考发挥失常,又大病了一场,最后只能去了一所普通高校,毕业以后当了个普普通通的员工。” “我加班半个月,有八天没有回家,洗漱都在公司。我替上司顶包,替下属擦屁股,七点四十赶着把文件送到老总的办公桌上,八点又要化好全妆跟着去出席晚宴。” 她的眼睛动了一下,路灯让她的眼里像是生出光芒。可她没有看过来,像是漫无目的地轻声说:“我长大了,没有成为了不起的大人;我焦头烂额,一点都不干净体面;我没有过好我的人生,也辜负了你。” 他认真地听完,半晌没有说话。他们之间隔了太多,隔着生死,隔着爱与失去,隔着十年的光阴草长。 她以为他也会怪自己,可他说:“这些年,你一定过得很辛苦吧?” 她终于崩溃,终于号啕大哭,在她心爱的少年怀里,像是沉醉在一场永远不会醒来的梦里。他就这样抱着她,耐心地等着她、哄着她。他是她永恒的避风港,是她月光下迟了一步的爱人。他像是在哄小宝贝,温柔至极地说:“这一次,我们没有误会,你没有生病,我也不会死在巷子里。没有‘祖母悖论’,颂白,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永远,多么美妙的词汇,她差点以为自己成功地挽回了一切。 可是没有。 她颤抖着用尽全身力气望向他,他多英俊,留在永远的十七岁,留在照片里,留在她的心里。 可他不知道—— “我做不到。”她说,“无论这一刻我们误会或是不误会,你死去或是不死去,冯嵇,我们都不能在一起。” “因为这一切,都只是个梦。” 她用攒了十年的钱,买来一个梦。梦里,她回到十七岁,她的少年还活着,一切还未发生,一切都能改变。 而当梦醒来,一切都不复存在。 “原来是个梦啊。”他恍然大悟,却又笑起来,“花十年攒的钱,只为了见我一面?颂白,你就这么喜欢我?” 她用力点头,哭得声噎气堵。他替她顺气,听她哽咽着问:“就算我害死你……就算我成了这样的大人,你也还愿意喜欢我吗?” 她等着,如同囚徒在等待最后的审判,可他却说起不相干的事来:“你记不记得那次,我差点害你淹死?” “那时我就在想,如果你死了,我也不要活了。” “还好我的心脏可以救下你,还好你能这样平平安安地活着。”他温柔地捧起她的脸,如捧着这一生最珍贵的宝物,轻轻地替她将眼泪擦去,“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无论你做了什么,我都会喜欢你,一生一世,至死不渝。” 她是他从小呵护的公主,是他不会悔转的美梦,是他这一生没有来得及开口的爱。 死亡将他们分开,却要爱永远夺目。 他做她月光下的爱人,永远定格,无从变迁。 丨原文《月光爱人》 丨载于爱格年9月刊 -往期文章- -好书推荐- 当当购买:点击上图即可 淘宝购买:中南天使图书专营店 点分享点收藏点点赞点在看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danhuaa.com/jdhhy/6871.html
- 上一篇文章: 这座欢乐浪漫的西南边陲小城,不仅好吃好喝
- 下一篇文章: 我是怎么成为ldquo我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