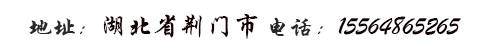25岁,要经历过多少场告别才完整
|
程少为在哪家医院坐诊 http://www.bdfyy999.com/m/ 尽管每一年都在数年龄 发现自己已经25岁时 还是吓了一跳 昨天醒来 梦见跟初中同学聚会 大家坐在原来的教室 原来的座位 原来的面孔和表情 这样的梦 我应该做过十几次了 有时候是小学同学 有时候是初中同学 高一高二高三同学聚会的梦 一个都没落下 回顾这些年来的告别 我一直以为是情感剥夺 忽然发现 它们使我更加完整 在25岁来临之际 我跟你分享下那些深刻的告别 它们不必一定具有意义 8岁,告别玩伴 童年的生活 回望是无穷无尽的欢声笑语 数不过来的五颜六色斑驳成影 我们去山间的清泉小瀑布抓小虾 去山上的丛林摘野果捡松柏卖钱 8岁那年的告别,是毫无防备的 想起郑重,就想起他的笑脸 我们吃完晚饭后约出去某个同学的家门口玩 每到晚上七点左右他们就从家里溜出来了 到我家窗边喊“暗号” 每次我做好自己分得的家务活就飞奔出去 有一项活动特别隆重 那就是每个小伙伴的生日会 基本都是在郑重家门口举办 因为他们家门口可以有灯 看得见可以玩游戏 寿星买了一大堆零食和饮料 小伙伴们都准备好自己的小礼物 现在仔细想想玩的什么游戏已经忘了 郑伟华是我们小舞队里面的一员 全队三个人,我领舞,他们在左右 每天晚上在伟华家“编排”舞蹈 其实就是几个人随便玩随意跳 舞曲是林俊杰的《就是我》 时至今日听到这首歌依然感动 伟华的二叔是我们小学的老师 教我哥哥的班级 在他们班里说我在他们家跳舞 类似于很厉害还是很拉风之类的 就这件事我被哥哥嘲笑了半年有余 那时候特别难为情 感觉小伙伴们的秘密基地一下子被公诸于世 后面再也没有继续跳舞了 他们相继离开去别的城市 郑重走之前咬了我的手臂一口 叫我不要忘记他 我们会永远是最要好的朋友 伟华走之前我们又去了一次小瀑布 山腰间有一个小水池 她脱光了只剩一条内裤跳进去游泳 让我帮忙看着 有人来的话告诉她 现在都记得当时自己很紧张 站在一旁看着远边的路 问她怎么胆子那么大怎么说脱就脱 一边说着十八岁时无论如何要相聚的话 分别时特别失落 我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是心里很不开心 让他们一定要常常打电话 打了两三年吧 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再见时早已过了十八 再见时有的人已经成家 再见时只能说说小时候的共同回忆 12岁,告别外婆 外婆家在村的另一头叫做西鼻 妈妈嫁给爸爸后搬去村的另一头 外公在我出生之前就永远离开了 记事起外婆独居在一个老房子里 我们家的小孩从小喊外婆“鼻嫲” 这个特殊的称谓我再也没有听过 小时候妈妈总会让我送一碗吃的过去 排骨玉米汤或是一些平时稀罕的菜肴 第一碗热气腾腾出锅,一定是外婆的 记忆中去她家的路上有一条黄土长坡 差不多到坡的时候可以一路跑下去 我还带过第二个妹妹跑 她摔得龇牙咧嘴 大门总是敞开着,她年纪大了很少出门 我边跨进大门边开始喊“鼻嫲啊在没?” 鼻嫲边应答从边左边老房子出来 动作慢悠悠地,对我笑说“来啦” 接过我碗里的食物倒进她的碗里 把我带过去的盛具洗干净放在一边 径直往右边一个废弃的小房子走去 她要去母鸡棚里摸鸡蛋给我带回家 她还要转身回房去床头摸索点东西 这是最令人兴奋又得假装淡定的时刻 因为我知道她在拿2毛钱准备给我 拎着装鸡蛋的饭盒蹦蹦跳跳回家吃饭 家里最小的妹妹比我小7岁 她出生后一岁开始由我带着 爸妈要做小本生意没时间照顾 我每天拿着妈妈发下来的一块钱 背着妹妹在村里各个小卖铺闲逛 多数时候当我们闲逛到鼻嫲家附近 一块钱零食也差不多被我吃完了 带着妹妹一起在外婆家门口玩泥沙 鼻嫲很少要求不能这个那个 这也是我喜欢去她家的原因 后来小舅还在院子里种了葡萄 当青葡萄刚刚结出果子时 她就开始跟我说几天几天后就熟了 我天天一进门就去看藤条上的葡萄 和她在待在一起时我们在旁边玩 她坐在葡萄棚下的椅子上,总在打盹 想起跟鼻嫲一起度过的日子 脑海中出现她家后边的桑树林 算起来以前吃过的黑桑果 应该得有几箩筐那么多 桑果还没熟透时我们已摘走一半 桑果开始熟透时黑得能滴出血来 进鼻嫲家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大碗 让我们吃够了再拎一大袋带回家 鼻嫲去世时72岁,那年我12岁 丧礼在村里的广场上举行 鼻嫲的棺材在正中间 她的所有子子孙孙们跪在四周 按照习俗家人请来一个班子演奏西乐 妈妈哭得撕心裂肺,双眼肿得跟葡萄一样 那是我第一次失去一位至亲 那时候我心里默默算着 我12岁,鼻嫲大我60岁 跪在都是黄泥沙的广场上两三个小时 我意识到再也没有人会回应我了 当我踏进大门一边喊“鼻嫲”的时候 什么声音都没有 鼻嫲永远的离开我之后 后院的桑树很快不见了 葡萄棚子也被小舅拆掉 我走进以前她住的房间 不变的是里面一片昏暗 回忆起帮她洗澡的时候 我问她小孩生出来多大 她指了指地上的热水壶 去年我在梦里见到她 她拄着一只拐杖对我笑 那是还年轻一些的阿嫲 大概只有六十出头的样子 神采奕奕地等着我叫她一声 我一眼认出她就是阿嫲 但是却忘了该叫她什么 还是没想起来 已经醒过来了 一晃时隔十二年已过去 原来还能以这种方式再见 14岁,告别爷爷 从小我们都叫爷爷“阿公” 阿公在我的印象中话很少 他一直戴着一顶尖头帽子 在他那个年代的老农都有 他过世前的一两年还在不停劳作 每天傍晚放学我有空会过去他家 离我家五六条巷子走几步路就到 远远地都能看到阿公在挑水浇菜 他的孩子们都让他别再那么辛苦 但他跟奶奶说一闲下来全身都疼 子女们拗不过他们只好任由作罢 阿公和阿嫲(奶奶)经常吵架 我还很小的时候在场不敢插嘴 后来长大一些了,胆子也肥了 我开始绞尽脑汁怎么去打断他 大多数时候都是他在指责阿嫲 我从小就勤快,学习比较用功 重男轻女的阿公阿嫲开始转变 只要我跟他们说学习进步等等 他们就饶有兴致转过头来听着 我还记得阿公侧耳倾听的神情 眯着眼睛笑盈盈地时不时点头 六七岁时我们跟阿公没分家 需要他抱着才坐得上长板凳 看他把我碗里掉出来的米粒 捡起来放进他自己的碗里吃 吃尽苦头,勤俭节约的阿公 每次给我钱“买文具”很大方 他默默地从口袋里拿出纸币 笑盈盈地说阿公给你买笔的 阿公生前那场大病发生之前 我还没听过“癌症”这个词 听说那时候的农村里头 得癌症的老人很多 确诊之后只能安静回家 阿公回家之后一直躺在床上 许久不见他过来 我问爸爸阿公怎么还没好 最后一次去看他的时候 他的床帘周围都遮挡着 阿嫲说来看阿公是孝心 你阿公知道一定很开心 但他可能没办法认出你 然后阿嫲带我过去床边 掀起床帘之前小小声说 你阿公瘦了别被吓到了 阿公瘦得只剩七十多斤 一身皮包骨头令人心痛 我小小声说了一句阿公 他好像不认得我是哪位 阿嫲一边在他床头说话 你孙女来看你了老头子 阿公轻轻地回应了一声 只有一个音节哼了出来 那一声那么沉重和久远 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聊天 不久之后阿公长辞于世 我翻回最后一次他给的 一张二十块钱的人民币 记得我当时在上边写字 阿公给我此生长存寄托 那时候哭是我以为他会 至少等我考上重点高中 像以前一样飞奔去他家 跟他报喜让他欢喜很久 但是他还是忘了我走了 阿公归仙那一年我初二 后来真的考上重点高中 后来纸币还是给弄丢了 17岁,告别初恋 小学升初中的考试正常发挥 毫不意外考了一百二十多分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成绩良好 后知后觉被转去重点班级 在这个班喜欢过一个男孩 初二学期开始之际 要去学校教务处交资料费 他就排在我前面两三位 看见这个后脑勺感觉熟悉 我问了旁边的好朋友 这位是不是xx 明明说的很小声 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转过头来 头一回我们的面对距离那么短 也是在那时候我看到他眼睛里瞳孔的颜色 是一种纯粹的浅棕,十分好看 眼神对上两秒之后他害羞地转过头去 我在心里想班里这个男孩长得真好看啊 他的物理和数学成绩特别好 因此我也能趁机经常找题目请教 他的话语不多 在一帮人的聊天里面他总是倾听 我总能看见他在人群中笑得开心 他十分善良,又特别聪明 一天他问我准备考哪所高中 一天我们开始在课间传纸条 有次他传来纸条只有四个字 笔迹清晰又整洁:我喜欢你 相约一起考同一所重点高中 纸条不再班里传了 我买了一本笔记本 开始两页三页地给对方“写信” 那时候我特别怕自己考不上高中 意味着要跟其他村里女同学一样 到一个厂里面打工 每天12个小时像一个机器低着头不停手 中考去别的学校考试 我们竟然被安排在同一个考室 一直以来都特别相信缘分的我 为这件小事偷偷开心了好几天 考试开始之前他不断地往厕所跑 算了算每场考试他至少跑了四五次 虽然他地综合成绩特别好,但是心理素质肯定没我高 中考结束之后 我们开始第一次名正言顺的约会 那时候特别流行去文具店拍大头贴 拍了好几版合照,其中还抱了文具店老板的小女儿入镜 那天我穿的运动服 他穿的黄色T恤和黑色七分长裤 拍完照是否还去买了奶茶我已经忘了 清晰地记得这第一次约会也是最后一次 而我们连手都没好意思牵 一两天之后我去东莞找姐姐打暑假工 每天通一下电话,那时候话费好贵 两人一边心疼一边数着时间聊天 直到中考成绩出来,他在电话一端给我报的分数 祝贺我们一起考上了省一级重点高中 我欢呼雀跃,开开心心准备回家迎接开学 故事到这曳然而止 之后与他失去所有联系 不再主动联系,不再回复 高中开学第一天 在学校碰到了,准备上前打招呼 他避让离开,我百思不得其解 三四年之后偶然联系 我说依然需要一个答案时 他的回答令我哭笑不得 如今他早已结婚生子 我们回归到初三之前老同学的熟悉距离 再也不会说起那段往事 也许这根本算不上初恋 它只是一件很小很小的小事 22岁,告别资金依赖 年5月20日大学毕业典礼 那年我觉得过得特别长特别慢 前半年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方向和未来 后半年没有信心没有自由没有笃定信念 有熬夜不头疼的青春 有一帮在操场吃西瓜的团建同学 有三两挚友去大学城踩单车 有信任依赖的男朋友 还有姐姐生的恒哥儿 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 我默默要求和答应自己 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家里要一分钱 领工资之前的所有开销我都先跟姐姐借钱 工作之后一个月一个月慢慢还 十月份的某一天 拿着工作的座机跟客人打电话 一边低着头做笔记 忽然感觉鼻腔凉凉的 放下笔还没来得及擦一下鼻水 哗的一下源源不断地滚出来鼻血 一边扯上几张纸巾捂住鼻子 一边镇定自若跟客人继续聊着 当纸巾被血浸透开始溢出 血一滴一滴地流到手臂,滴到键盘 我才跟客人道歉挂断电话 我站起来环顾四周,没有人 大家都在会议室开会 我本来也要进去开会的刚好在接电话而已 我跑去厕所清洗 鼻血不断流出来,一直流出来 出来时看到Tony叔叔紧张的神情 原来他在我跑进去厕所前注意到了 二话不医院 医院见到医生时还在流血 医生说当下没办法处理 只能用棉棒塞住强制止血 后来检查是鼻腔内毛细血管干燥破裂 说做一个微型电焊处理就能永久治愈 那个处理花了我半个多月的工资 当天回去办公室六点多 手头上的工作推积如山 无人问及是否需要帮忙 我加班工作到十点多下班 我跟上司申请第二天休息 被委婉拒绝 理由是我休息了这些工作谁做 我是一个协调员 要支持几名销售经理的工作 如果我没人协调他们做不完 我点头 插着一根浸满血的棉棒在左侧鼻孔 暂时不去面客就好才不影响公司形象 正常上班在各个部门游荡 叔叔眼神很哀愁,摇着头对我说 我们只是一颗螺丝钉 如果坏了不能运作了 他们会头也不抬继续找下一颗 一个月后 我带着一个客人在看场地 介绍着细节时忽然又开始流鼻血 跟客人道歉后让其他同事帮忙接替工作 跑进厕所后一边用纸巾捂着鼻子 一边不争气地掉下眼泪 不是说了会永久治愈了吗 为什么出尔反尔 看完医生回去公司路上 上司发了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danhuaa.com/jdhhy/6150.html
- 上一篇文章: 河源装修设计别墅庭院常见植物种植
- 下一篇文章: 小明,请用北和南遭词胡萝北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