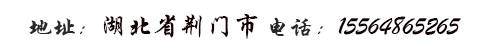本怀读诗精华版十八
|
白癜风治疗价格 http://pf.39.net/bdfyy/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遇见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遇见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遇见 故乡的原风景 这首绝尘之作《故乡的原风景》,来自日本陶笛大师宗次郎。宗次郎先生在创作这首佳作诗,宜居到了栃木县东部的茂木町,在远离尘嚣的环境中,归于大自然,耕田、劳作,并用自己制作的陶笛,吹了出这首满溢诗意与禅意的作品。 同时,它也是《神雕侠侣》的配乐,看过这部剧的人,对这段旋律一定有很深的印象。 当小龙女跳崖的那一刻,这首音乐的悲凉气息被发挥到了极致,和剧情配合的天衣无缝,陶笛深邃的旋律,让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跃然于耳畔,感染着每一个观众。 拉萨的春天 本期作者08January 木桦淳本津渡马振霖王厚朴 金铃子孟怀球向以鲜臧海英邓玲 我是她的坟 木桦,80后诗人,生于辽宁铁岭,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曾出版诗集《眼底世界》。现居北京。 妻子化疗时 老是胡思乱想 最纠结的问题莫过于 死后埋在哪儿 埋我老家,她觉得 孤单,毕竟我还要继续北漂 暂时不可能回去陪她 埋她老家,又不大可能 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骨灰 在她父母那边,风俗比天大 妻子转过身,低声哭泣 留给我一个光滑的脊背 她说死后连个安身之所都没有 我从背后紧紧抱着她说 你死之后 我会把你的骨灰盒 随身携带 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 妻子转过身 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知道,在她眼里 我已经变成了一座满脸络腮胡 后蹄儿直立 且能自己移动的坟 点评读这诗,我感到了一份契痛,更感受到现代人之漂泊无依。 妻子化疗之时,想到死后该在哪里安放自己的骨灰,并因此而“胡思乱想”,这很正常,“她说死后连个安身之所都没有”并因此而纠结,亦很正常。“埋我老家,她觉得/孤单,毕竟我还要继续北漂/暂时不可能回去陪她”“埋她老家,又不大可能/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骨灰/在她父母那边,风俗比天大”,这两者都为难以改变的现实,前者里有爱的情愫,后者则有根深蒂固的习俗。作为一个正值盛年的女人,死后既不能跟随在爱人身边,又无法回到父母身边,如此两难,情何以堪? 解决之道最终为“我是她的坟”。“我从背后紧紧抱着她说”与“妻子转过身/直勾勾地看着我”,细节足以见证我们的一往情深。于“我”而言,也许只是善意的谎言,毕竟骨灰盒放在家里会让孩子感到害怕,正当盛年的“我”也未必不再为孩子再找一个妈;于“她”而言,则无疑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因“直勾勾地看着我”,不难感受她在绝望里闪烁出的希望火花。 本诗精彩之处在对“坟”这个意象的独特建构。“我”的身体与“坟”之间本有着莫大距离,却因“妻子转过身/直勾勾地看着我”而得以融合。倘若“我”按承诺将妻子的骨灰盒带在身边,“在她眼里/我已经变成了一座满脸络腮胡/后蹄儿直立/且能自己移动的坟”便不仅为她此刻的感觉,更为她心底已被确认的事实。 另外,“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骨灰”应为对俗语“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之仿写,因其中骨灰对水的替换,让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有了更深切的无奈与悲伤! 室 淳本,女,黔人。七零后,居贵州凯里。出身书香,以为诗即是生活。诗作偶见诸报刊杂志及选本。获年“第二届淬剑诗歌奖十大女诗人”奖。著有诗集《时光的盒子》,《汉歌隆里》。 一个人坐在,等待敲门的人 或许是个送外卖的 披着露水,掠过了朝生暮死的小城 或许是个猎人,要送我一只惊慌失措的野兔 或许,是我的爱人,他只是来看看,而已 或许,只是寂寞 与我一样,轻轻地用手拍拍世上的任何事物 咚咚咚,咚咚,咚 点评独处之时,很多人还是希望有个人来敲门,甚至,不管他是谁,只要是个人即可。这源于人终究为群居动物,生命深处的群居基因决定了没有人能够或者愿意将孤独永远持续下去,本诗所呈现的也许正是人的这种本能。 这,是家里,还是宾馆?两者都有可能。据此是否可以认定,诗歌主人公还处在独身状态,甚至长时间独居。只有在这样一种情状之下,她才会如此渴望有个人来敲敲门,哪怕只是个送外卖的都可以。而据诗中所呈现,这,可能在城里,也可能在林中;有可能为真实的一间房,也有可能只在她想象里存在。 就表达而言,全诗有一个逐渐由实向虚的过渡。如果说之前她等待着的场所有可能只存在于其想象之中,但她所等待的那些还是相对实在的人或物,而一旦抵达“或许,只是寂寞/与我一样,轻轻地用手拍拍世上的任何事物/咚咚咚,咚咚,咚”,那么诗歌主人公便有可能连同她的进入到一种彻底的空寂,本诗也因此有可能成为中国版的《等待戈多》。 山月 津渡,年生,湖北天门人,著有诗集《山隅集》《穿过沼泽地》《湖山里》,散文集《鸟的光阴》《植物缘》,童话集《大象花园》等,现居上海。 落在石隙中的月光,落在锁孔里的眼珠 房舍,像是蛋糕上镶嵌的水果 但是这些都只是一刹那间的幻影。一座座山,缓缓地撕裂 张开大口,对着夜空喘息 夜风中,星星闪烁其词,我暂且忘记了言语与诗行 点评“落在石隙中的月光,落在锁孔里的眼珠”,这个比喻为对山月(月光)的正面描写,因这个比喻,读者自可感知到这石隙的深邃与幽暗,也可感知到这山月的轻盈与灵动。随之而来的诗句则为对山月(月光)的侧面展示。“房舍,像是蛋糕上镶嵌的水果”,如此比喻可谓绝妙,足以见证山之博大,“但是这些都只是一刹那间的幻影”则显示了山月照拂之倏忽,这倏忽感应该在山里才会有,平原地区房舍上的月光肯定不会如此快地消失,这证明房舍有可能被树遮住了,或者被另外的山峰遮住了,这才会导致漏下来或斜过来的山月一晃而过。 山本应静,尤其在夜里这静更加明显,然在,在诗人意识里却“一座座山,缓缓地撕裂/张开大口,对着夜空喘息”。仅从字面来看山的动感甚为强烈,但这甚为强烈的动感,所衬托出的却应是月的宁静,纵使山有千变万化,那月却亘古清冷。 至于那一座座山,为什么“缓缓地撕裂/张开大口,对着夜空喘息”?或许因它们在这俗世,也免不了藏污纳垢,希望此刻能在这清辉里尽情地沐浴、吐纳,以便在月色里再次回到清新与纯粹。而诗人在那一刻,一定将自己也纳入到了那一座座山的行列之中,也希望能借这山月回归生命的清新与纯粹,而“夜风中,星星闪烁其词,我暂且忘记了言语与诗行”则正是这回归的见证。 他终于应了一句话 马振霖,原闽东青年诗歌协会秘书长,福建日报高级编辑,原海峡导报社社长。 枯叶知秋落到他的身上 花朵点缀白发 坐在红鸡蛋树下 红鸡蛋花花期很长 只有风吹过,空旷的湖畔 吹过不动的嘴角 不知道是他忘了时光 还是时光铁锈他 夕阳坠下山崖时叫了一声 他喃喃应了一句话 答对没答对,他自己都不知道 风一下子立了起来 点评这首诗主要应在呈现某种感觉,这感觉比沉默还要沉默,倘若不是那“夕阳坠下山崖时叫了一声/他喃喃应了一句话”,则诗中情境简直可用死寂来形容。至于诗为什么如此沉默,乃至死寂?这一方面源于季节,另一方面则源于年龄,另外还因“坐在红鸡蛋树下/红鸡蛋花花期很长”。 红鸡蛋花在诗中也许并非只是自然里的一种花,它极有可能还是诗歌主人公某种人生期待的象征。假如像这样解读,第一段的沉默就可理解,并且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往事不堪回首,乃至于往事不愿回首,在那样一个时刻,除了沉默之外,难道还有更好的应对吗?“不知道是他忘了时光/还是时光铁锈他”则是对那种状态精准的刻画,在那一刻,时光与他之间或许早已相互锈蚀了吧。 至于“夕阳坠下山崖时叫了一声”则为通感。即使那夕阳坠下再震撼,它恐怕也开不了口,诗人是将其有视觉上的震撼转化为了听觉上的突然,这应该只是潜意识地听到,他在那一刻“喃喃应了一句话”则为一种本能回应,“答对没答对,他自己都不知道”以及“风一下子立了起来”则为“夕阳坠下山崖时叫了一声”所制造出的主客观效果。就整体而言,本诗应重在感觉,而非感悟。以我的理解,在诗歌创作中感觉应为其主体,感悟则主要画龙点睛;诗的感觉可以弥漫于全诗的每个角落,感悟则应集中于某一点;就一首短诗而言,能在某个方面有点感悟就已足够,倘若通篇都在拼命地表达感悟,那这样的诗一般难以卒读。 回乡偶记 王厚朴,年生,籍贯陕西商洛,从医。王厚朴,年生,籍贯陕西商洛,从医。 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红旗新村81栋号 途径21县市 多公里 到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土门镇七星沟2组5号 我带回了: 双氯芬酸缓释胶囊3盒 消痛贴膏6盒 铝碳酸镁咀嚼片11盒 奥美拉唑胶囊8盒 辛伐他汀片9盒 阿司匹林肠溶片7盒 …… 整整一大包药 我打开它们 像十九年前,父亲打开他从秦岭山带回的珍宝 糖果、气球、钢笔、鞋子、陀螺、水枪、弹珠、 手电筒…… 我的爱好真多 父亲的病也是 点评本诗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具体。诗中既有“我”回乡的行程,也有“我”带回来各种药品的名称。如此呈现似乎没什么价值,更没什么诗意,因这呈现读者却可以感到“我”回乡的路程遥远,回一次家真不容易,而因“我”带回来各种的药品,读者也肯定认定父亲的身体状况实在有些令人堪忧。 本诗给我的第二个印象为因对比所传达出的苍凉。不过十九年过去,父亲却早不再是当年那个生机勃勃的父亲,“我”也不再为那个“爱好真多”的“我”。当时中年的父亲早已抵达老境,而年少之“我”也已跨境中年。当年“我的爱好真多”,此刻父亲的病真多,这两多虽然隔着一条不长不短的时间之河,却流淌着亲情,更流淌着苍凉。 读完,我情不自禁地叹惋:人人都不愿意长大,但谁又可以不长大?人人都不希望变老,但谁又可以不变老?而诗中之“我”在当下何止成千上万:当回不了家,他们自有无穷无尽的牵挂;偶然回家,却又难免一言难尽的唏嘘。 这人生 金铃子,诗人,书画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国家画院曾来德工作室访问学者。著作有诗画集七部。 抄袭和复制,已不可能 从头再来,已不可能 投胎转世,已不可能。索性坐到天亮 索性把爱过的人恨过的人拿来祭祀一下 索性放声大笑 把他们笑活,又把他们笑死 点评诗之美,从来就没一个统一标准。比如中国古典诗词多追求含蓄,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与李清照《夏日绝句》却均以直白取胜,并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这人生》也属直白之作,不但全为大白话,而且说得斩钉截铁。那连续三个“已不可能”,不但将人生不可再来之意蕴表达得完全彻底,而且也为随之而来的三个“索性”做好了心理铺垫。 这三个“索性”,相对于那三个“已不可能”,显得更具体、更生动,也更有现场感,还特能凸显诗歌主人公之个性特征;而由这三个“索性”,读者不难感受她的随意率性,不难感受她的干净利落,也不难感受到她的豪气干云。 既然“索性把爱过的人恨过的人拿来祭祀一下”,说明那些人于她都已成过眼云烟,爱过与恨过不再有任何差别,这与普希金“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相差无几,多了一个“祭祀”,则让这怀念更具有仪式感,而仪式感于日常生活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至于“索性放声大笑/把他们笑活,又把他们笑死”,则不但打破了“祭祀”那一以贯之的严谨与静穆,还化事实上的不可能为想象里的可能,让其快意、率性的性格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在此,我想多说一句:写诗并无定规,不管用什么方法写,都有可能写砸,也都有可能写好,关键靠感觉与把握;在此不妨套用一句教育人的老话:诗无定法,诗必有法,法在诗中,随机而法。 自白 孟怀球,70年生在华容,17岁闯海南下,打工创业成家,27岁复北上漂泊,经营酒店服务业,小有所成,37岁回岳阳,以一片茶舍营生,闲来好读好写好玩好四方行走及运动,远烟远酒远赌远不良之应酬,曾有《幸福之门》《梵心集--乡诗三百首》,《听雨,问禅》出版。 我喜欢花花草草 喜欢诗酒茶趣 喜欢交几个无用之友 喜欢读一点小文章 喜欢说几句大实话 喜欢质疑权威下的教化 喜欢探究灾难后的真相 喜欢自由行走在乡野 喜欢独立思考在午夜 喜欢认真的生活 喜欢纯洁自然的真善美 喜欢蔑视无聊的假大空 喜欢静坐窗边 喜欢在今天傍晚时分 与你一起分享这绚美的天空 喜欢和彼此期待的人相聚 喜欢去风物俱佳的陌生城市 喜欢山青水秀的太平盛世 喜欢忽然间为你 写下一行行惊艳的文字 7月8日午家中 点评“我”的自白,最终喷发成这一连串的“喜欢”,而如此多的“喜欢”虽然为一时间脱口而出,却一定在其胸膛里蕴藏了许久。通过这些喜欢,读者自然可感受到诗歌主人公的情趣,也可感受到他这些年来的坚守,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有着敢于质疑的品格与独立思考的习惯,并敢于将自身的质疑与思考公之于众,而在当下,善于藏掖、口是心非的诗人却为数不少,其人与其诗之间往往存在着极大的落差。 这一连串“喜欢”既让读者感到具体,因它们已经涉及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又让人感到实在,其中不但没有时常喧嚣于耳畔的高大上,反而对那些假大空表达出了明确的质疑与厌恶。同时,即使现实没多少岁月静好的诗意,仍不妨碍他有对愿景的坚信与追求,而诗中那个“你”,或许为诗人之爱人与情人,或许就是他的另一个自己。 就表达而言,既然诗题为“自白”,这诗也就难免直白,但这直白里既有冷峻,也有炙热,既有质疑,也有展望,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他敢于袒露自己的胸怀,真正做到了怎么想就怎么说,甚至还期待着怎么说就怎么做,但愿在时间流逝里,他的这些“喜欢”都能够如期而至,也但愿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能够因这些“喜欢”而变得真正美好。 制鼓的老人 向以鲜,现居成都。诗人、四川大学教授。有诗集及著述多种,获诗歌和学术嘉奖多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同仁先后创立《红旗》《王朝》《象罔》等民间诗刊。 他已经很老了 老得再也抡不起斧头砍倒 一棵比他更老的柏树 老得再也无法看透 一张水牛皮是十岁的牛皮 还是八岁的牛皮 制鼓的老人 想用自己那把老骨头拼一架 有几分骨气的鼓腔 用饱经苦难和风雷的人皮 做一副鼓皮,给寂寞的世界 留下一点儿响动 点评读完这《制鼓的老人》,我很以为它就是诗人的自白,而这“制鼓的老人”,则应该就为其自身。当然,我也不排除现实里确有这样一个“制鼓的老人”存在。 我之所以会如此认定,是因诗的后两段。“制鼓的老人/想用自己那把老骨头拼一架/有几分骨气的鼓腔”“用饱经苦难和风雷的人皮/做一副鼓皮,给寂寞的世界/留下一点儿响动”。作为大学教授的向以鲜,在生存处境上肯定远优越于这位“制鼓的老人”,而其年龄与身体也未必就“老得再也抡不起斧头砍倒”,更不可能“老得再也无法看透/一张水牛皮是十岁的牛皮/还是八岁的牛皮”,但在要给这人世间留下一点骨气、在这人世间制造一点响动上,二者却应该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或许这正是诗人即使人过天命依然勤奋写作的根本原因。 因此,我认定诗中“制鼓的老人”只是“外象”(物象),而那个一直没出场的“我”才是本诗的内象(意象乃至心象)。因此,这首诗貌似在写那位“制鼓的老人”,实际上却主要凸显了那个隐藏于诗里的“我”。 身体论 臧海英,山东宁津人,暂居德州。 我们使用它。 触摸它容器一样的四壁 它确实承载着我们非物质的部分 存在的证据 每次,我们指向的也只有它 当世界回到一张床上 谢谢你的身体 谢谢我自己的身体 有时也讨厌它 它无节制的欲望 以及对另一个身体的移情别恋 我们最终 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力 ……到了安慰它的时候了 侍奉它的疾病和衰老 看着它从我的母亲 变成我的孩子 .2.24 点评读这首诗,或许你会因此而对身体有清醒的认知,真正做到以身体为友;既享受身体所带来的方便与快乐,又一辈子与身体做朋友,相濡以沫,并因有个好身体而有个好人生。 身体,本为抽象名词,却被诗人演绎得具体、生动、完整,其中既有感性的展开,也有理性的小结。“每次,我们指向的也只有它/当世界回到一张床上/谢谢你的身体/谢谢我自己的身体”,由此你是否回味起那曾经的亲密无间,并因此而感谢自己与对方的身体;“有时也讨厌它/它无节制的欲望/以及对另一个身体的移情别恋”,由此你又是否想起了别人的故事或自身的经历,并因此对“贪得无厌”“见异思迁”等成语有更为真切、深刻的理解;“触摸它容器一样的四壁/它确实承载着我们非物质的部分”则为对身体与灵魂关系极为具象的呈现,相对于灵魂的轻盈与隐秘,身体的确就是这样一个具体、清晰又有些沉重的容器。 “我们使用它”“我们最终/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力”,如此论断足够冷峻,揭示了关于身体与生命的真相。没有谁会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谁对自己的身体都不过拥有数十年最多上百年的使用权而已,并且所有人对身体的使用权最终都将被收回,古今中外谁又可以长生不老呢?尤其是在每个人生命的终点,身体都可能脱轨,难以再保持之前的常态,并在各种各样的异常坠落到黑暗的深渊。 总体上看,这首诗在内容上无疑做到了深刻,因为它所揭示的为关于身体的真相与本质;同时,这首诗在表达上做到了感性与理性交相辉映,即使其中的某些细节,也因得到了提炼并而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 雪花 邓玲,网名幸运相随,湖南长沙人。系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四川省楚文化研究会书刊编辑出版院执行秘书长,四川省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理事,四川省德阳作协常务理事,张家界诗歌学会会员,娄底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被众多网站,平台及文学刊物刊发。 诗观:必须在诗意中活着! 如此晶莹剔透的美好 不是这人间 便可悟得到的 例如今天早晨 打开房门 迈出一只脚 又不愿落下 这种禅 不是所有的花 便可悟得出的 例如视野 谁和我一样 松开自己 又抱紧自己 这种心情 不是水 就可以悟得透的 所以,我不动 你动 只要你不怕 疼出声音来 点评我喜欢本诗所传达出的那份轻触感。其实,某些情境,某些情愫,不管你是否感受到,它们一直都在那里,其美好也一直在那里。当然,这要有人去感受,更需有人去珍惜。比如读“打开房门/迈出一只脚/又不愿落下”,“我”为什么脚迈出了又不愿落下,这其中一定有理由,除了眼前“如此晶莹剔透的美好”的客观,恐怕更有她那发自心底的对纯洁、美好的怜惜与悲悯。 如果说“例如今天早晨”所展示的情景还较为客观具体,那么“例如视野”则不免有些主观抽象,“谁和我一样/松开自己/又抱紧自己”,这“松开自己”与“抱紧自己”不仅为两种身体姿态,估计还有着相当复杂的心理背景。而究竟为什么背景与原因,诗人却不说,她甚至认定“这种心情/不是水/就可以悟得透的”,上善若水任方圆,既然到了水都难以悟透的地步,那又何必再与人说三道四呢? 当然,对本诗的解读也无需过分玄虚,毕竟它有个明确的诗题“雪花”。有了这“雪花”,首段之“晶莹剔透的美好”、第二段之“迈出一只脚/又不愿落下”、第三段之“视野”便都有了着落,末段那“我不动/你动”也不妨认定为“我”面对大雪飘飘的剪影,诗中之动静既有对立更有融合,“我”与雪花则可能因“打开房门”而瞬间主客观相互渗透。 同时,“我不动”也足以让“我”在那一瞬间的姿态变成一尊雕塑,“你动”则仿佛眼前正在播放大雪纷飞的视频;诗所呈现本应为“我”面对那清晨晶莹剔透的雪地不忍踏下,却转移视线与立场,反而让那纷纷扬扬的雪花生怕“我”“疼出声音来”,如此之移情,让诗之前的怜惜由单向变成双向,并因此凸显出雪花于物质的美丽之外,更有那精神的美好。 推荐阅读 年鉴本怀读诗 本怀读诗:五月牛五首诗 本怀读诗特刊║读诗札记之三 本怀读诗:明静五首诗 本怀读诗:岳上风五首诗 本怀读诗:喻言五首诗 本怀读诗:留言集锦之二 小编的诗 洗白了 文/拉萨 那个从煤场走岀来的人 脚印 一步一步被雪 洗白了 -01-07 拉萨厨房 长按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danhuaa.com/jdhzp/8784.html
- 上一篇文章: 四月书影音ldquo焦虑是让你改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