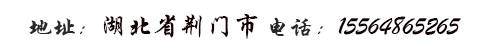记忆中的泗洪青阳老街
|
泗洪记忆——青阳老街 青阳街最有名的地方该数花园口,它是泗洪县城的新街口,十字大街交叉处一开始有一个花园,大约在年左右。当时泗洪还没有一辆汽车或拖拉机,大街上牛车,马车,板车,独轮车已经算是与这条大街相当匹配了,有居民家的猪羊有时兴之所至也会在上面逛逛,一个直径五十米的花园一点也不影响交通,反而把大街搞得多少有点紧凑和充实,有凝聚力。花园里开始种本地花卉,什么月季,大黍花,蝴蝶花等,一到冬天基本就只有霜花、雪花了。过年时还有烟花。花园口一度被浪漫人士用木料芦席搭成天安门,以示敬仰,风头过去又改了回去。花园原来的木栅栏改为铸铁的,基座青砖改为水泥沙子混凝土,离自然越来越远了。里面的地方花草改为冬青黄杨,老百姓也有三分奇怪,知道了不仅松柏在冬天不死,还有其它。过了几年车多了,花园口改小了,又过了几年花园口改没有了,中间放了岗亭,有人在上面指挥交通,到了后来岗亭也没有了,只有地上划得斑马线,直行线,转弯线,黄线,停车线,空中有红绿灯。 到花园口折向东原来是百货公司,全县最高级、最全面的购买都在这里,后来被大润发取代,对面是泗洪电影院,它曾经比女人还有魅力地吸引我们好几年,那几年我们几乎把青春、生命、灵魂都交给它了,我们以地下游击队的手段看了《地下游击队》,我们以看不见的行踪看了《看不见的战线》,有时为了看《追捕》不幸被看门人追捕。因此,我们似乎是有信仰的人,百折不挠,无怨无悔继续以前的追求。我们进入这里就是进人天堂,“荣幸”二字在这里体现得最完美。 从这里向前得向北转弯了,不然向前是南小街,紧靠的是汴河,河边有后来倒闭的小糖厂、绞绳厂,石灰窑场,早年能看到张侉子在绞绳厂门前做扩胸运动。有人说他埋在肉缸里也不会胖,其骨瘦如柴的体型总叫人以为他在带病工作,也有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其实他身体好得很。一顿三碗饭还舔锅铲。从这里再向前不远,汴河就转身往南去,就是郊外的村庄二里坝,三里坝,一直到临淮了。 向北,过了南大桥,就到了青阳街中心地带,在桥上可以看到老汴河以及记载中的老汴河十景的部分痕迹。白云落影啊,柳枝拱合,浓荫匝地啊。旭日筛林这四个美景就简直妙不可言了,谁理解了,谁就是诗人,谁就懂了民间生活,还有夕阳垂辉,烟村耕耘,白帆竞发,虽说平淡一点,也是美不胜收。大桥原来是木桥,直到从上面低头可以看见桥底的情形,上级才更换木板,随之不久在一旁修建了一座全水泥石头的拱桥。此时已有汽车通过。老桥桥墩在拆除时费很大力气,炸药都感到为难,远不像今天一些桥梁,你不动它人家都会自觉倒掉。 青阳核心部分在濉河、老汴河交汇后又很快分开的夹角里,也就是一个三角地带。濉河来自河南陈留,汴河来自河南开封,许姓祖地也在河南登封,所以我们很少说河南人坏话。 青阳地名的来历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志书为证:“青阳古国名少昊,青阳氏分支子于此”。青阳本是复姓,可以说是青阳镇最早的姓氏。其二是民间传说,显然文学化了,说是很久以前,青阳原名青羊,是五色羊云游天下,青羊留在这里,演变为青阳,其他四色羊分散在东西南北。而中华大地叫“青阳”的不少,它们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一项不关心这些追根求源以致无聊透顶的事情。 青阳镇历史上行政称号是不断变化的,有集、寨、镇、关、汛等名。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大汶口文化这里也不稀罕。根据史载,青阳氏是黄帝(轩辕)之子分封于此。黄帝有4妃5子,分为1姓,古之姓氏是由此开始的,青阳氏就是其中的姓氏之一,距今已有多年。这或许可以满足我们青阳一点老资格和“历史悠久”的虚荣。 青阳镇属徐国,那时国家很多,只要有点势力,成立一个国家好比今天注册一个公司还那么容易。青阳原有一座皇姑庵,相传是徐偃王皇姑修道之所,解放前曾有人在庵中拾到金砖。国民党团长曾经把团部设在里面,黄鼠狼咬断了电话线,野猫抓破了他的脸,老鼠打翻他的油灯差点把他变成烤鸭,后闻之此庵来历,吓出一身冷汗,连叩三个响头,求姑奶奶恕罪饶命,遂移师桥南。 由于青阳在当时是水陆交通重镇,谁占有谁就可以丰衣足食,仗势欺人。《泗州建置沿革表》中记载:徐国在春秋时期为吴国阖閭所灭,越灭吴后又属越。战国之初,楚灭越,属楚,考烈王畅春申君淮北1县,为此,青阳没有少参与争斗,虎去狼来,貌似热闹,只是苦了老百姓。 青阳为泗州首镇,东西水陆二路必经之地,西去长安,东去江南,这里都是首选的捷径,当年修路不易,人工或自然形成的水路正是悠然自得的通道,那时的人多无急事,大多数人都过着散淡的慢生活,他们不懂时间就是金钱的真理,也少有奋起直追,跨越争先的意识,优哉游哉才是人生,那种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成败在天的宿命信条在平民中间很有市场,一直畅销,因为没有火箭和电子,也就没有了浮躁和焦虑,他们忘乎所以,漂泊在水面,到哪是哪,时间属于上帝的,人类不掌握时间,只释放性情。不设计人生,只考虑生人,传宗接代。 到了隋朝,隋炀帝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大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青阳地段的古汴渠,上接通济渠,下连山阳渎,是汴东地区一个重要关津。有人总在抨击隋炀帝残暴奢靡,我觉得他可贵在于能做事,做成事,比起那些仅仅残暴奢靡之徒还算是好的,若不是他的残暴,哪来的大运河?也就是说哪来后代的福祉?再退一步说,比之那些昏庸无为的人,他又是功不可没的,有时候不动点粗真还不容易办好一件事,你要不栽树,后人怎么乘凉,你若说栽树很麻烦,就算了吧,还是打牌喝酒吧。后人不骂你无能吗?我们前辈的流血牺牲不也就是为了下一代过上好日子吗?当然我们的先辈和隋炀帝有本质的不同。总之,不论手段如何,给后人留点好东西总是值得肯定的,秦始皇如果是一个软弱无能,碌碌无为的人,哪来万里长城?没有万里长城,难道今天中国不缺少很多值得骄傲和显摆的东西么?就青阳而言,不是隋炀帝,哪来“皇姑庵怀古、碧霞宫晨曦、城隍行宫落照、玄坛庙晚钟、汴水清波、隋堤烟柳、重岗山蜿蜒、汴河渔火、三步两桥、一步两庙”的十景名胜呢。 青阳的城隍行宫也叫隋炀行宫,它前临汴水,背依濉河,三面环水,初建时分前殿、正殿和几间僧用配房,一座钟亭,均为砖瓦结构,隋炀帝第二次南巡时,沿途建许多行宫,这个城隍行宫受到重视,改建扩建,用现在话说是提升,无论大殿,还是后宫,还是廊庑,以及花园,亭台都不亚于中南海部分景观。 到唐宋时期,古运河就更加成为中央统治的生命线。没有交通,就谈不上军事的控制,物资的调运,信息不畅,鞭长莫及就是这样。鉴于此,沿途重镇也得以更重,“青阳关津”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了小城镇的建设,当时青阳一带运河“水阔而深。帆樯杂沓,商贾云集”,真像宋代诗人诗中描述的那样“官舻艑客满淮汴,车驰马骤无间时”。到了北宋政和元年(年)青阳镇的名称出现。 明末清初,运河古道虽已废,但是青阳到洪泽湖段依然水流幽深,渔民每天早晨来桥头卖活蹦乱跳的鱼,农民来卖青枝绿叶的蔬菜,水淋淋的莲藕,湖边人来卖柴草,都是顺着汴河逆流而上。青阳为汴东地区一大走集,逢集期(农历每旬三、五、八、十日集),四乡之民汇集于此,牛市街就是买卖牛的地方,买牛不是小事,得请内行人看牙口,看精气神,买牛不是吃肉,而是拉犁耙地,农业是青阳地区之首,所以牛市生意兴隆,也充满暗流和诡计,行老板不仅是纵横的说客,还是地方一霸,要镇住这个场面没有三斧头,谁也不敢担此重任。西大街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有官府,有大牢,也有戏园子,到了清代,镇内住家余户,多姓朱、席、梁、陈,有四大家之称,后又兴起许、石、江三大财户取而代之。不久四大家就风光不再,或流落他乡了。嘉庆年间,泗州举人知州正堂郑裕中曾带领宾客00余人,浩浩荡荡而来,到其妻许氏府第祝寿,交赠寿匾一块,上绣有“松操柏纪”4个大字。领导关心,捧场,许姓再掀高潮。 青阳在明清时期为税务关卡,桥头竖有一面红色旗帜,上书“税务”二字,雁过拔毛,况乎商贩?。民国7年(年)由军方(军阀)所管,故地方志上把青阳又称其为青阳关。这里还开了隆源、恒权、同和、兴源等8大糟坊。数十家酒、油作坊,有南义和、北义和商店,高记杂货,喻记药铺,杨记棉庄,万顺银楼,反映了青阳镇经济复苏。隆源酒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得以重建,在老米努力下辉煌一段时间,老米走了,人走茶凉,酒也不香了。当时在台湾的青阳人写信回来还用”安徽省泗县青阳镇隆源槽坊”这个地址呢,喻记药铺来自江西,喻家女儿喻尊霞后来成为抗日英雄,把刑场当着唱歌的舞台,着实把日本鬼子吓得不轻,也为青阳增添不少光彩。 古镇青阳、占地千余亩,全镇1条大街:西大街、沟西街、瓦滩街、牛市街、鸡心街、前街、敞巷街、弯子街、南小街、东小街、桥南街、新集街,街心均系条石铺砌。街两旁楼房店堂、作坊鳞次栉比,错落勾连。有七座桥:汴河桥、蛮子桥、北门桥、疑方桥(又名迎芳桥)、太平桥、东门桥、拦架桥。14座祠庙:城隍庙(又名城隍行宫)、玄坛庙、碧霞宫(又名奶奶庙)、火神庙、三宫庙、皇姑庵、茶庵庙、许氏祠堂、江氏祠堂、石氏祠堂、玉皇庙、礼堂、龙王庙、恶水庙。城郊北有程家庙、西有房寺。建筑格局很有都市的风貌。在诸多寺庙中以城隍庙最佳。原青阳寺庙众多,四乡八邻多来敬香,求神拜佛的人络绎不绝,这给古镇青阳也增加了浓厚的佛教色彩。有三月初三玄坛庙会、四月初三骡马大会、四月初八城隍庙会之风俗。人们在对同类失去希望的时候,基本都寄希望与神灵,青阳庙之多,也是因为信徒之多,信徒越多,政权就越容易失去权威。 青阳许氏明万历年间来自安徽黄山地区,在先是从河南许昌一带到了安徽。许氏家族,艰苦奋斗,与人为善,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家族发展很快,五百年前来此地仅弟兄三人,如今已十万余众。祠堂是一个家族的象征,是家族族权的中心,族长虽说是议会制,但权威达到可以判决家族之人忤逆的死刑,也可以调节兄弟阋于墙的琐。许氏旧祠堂建筑较早,但工艺不尽人意,也与许氏家族当时的影响力不匹配,于是许氏头人和家族芸芸众生一致决定在乾隆年间重建。重建的许氏祠堂正殿为三明二暗,五间大殿。明间供先祖排位,暗间有阁楼。青砖垄瓦,高大雄伟,威然壮观,是当时青阳城里标志性建筑之一,故有江氏祠堂、许氏楼之说。请道光皇帝御赐许联镖铜铸隶篆“寿”字花匾,安坐祠堂脊顶正中,使许氏祠堂熠熠生辉。许、石、江都有亲缘姻缘,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不清,道不明,既光明正大讲交情,也暗暗较劲比赛,你追我赶美化祠堂,争脸面。可惜,解放后,祠堂被取消,因为这些场所容易转移老百姓对政府的注意力和向心力。 江氏祠堂,坐落在瓦滩街北首,坐东面西,是一所深宅大院。整体布局为大门、前殿、正殿、学堂。南北有垣墙围护,高约丈余。大门两侧石狮,形态逼真,威严端座。大门楹联为:“世泽于今光泗水,家声自古振兰陵”,“江氏宗祠”大匾横悬上端。进正门经前殿向后行便是正殿,高大雄伟,飞檐翘首,“鸡爪寿”吉祥物悬于正殿脊顶,召人眼目。正殿门楹联是“木本水源勿忘祖德,秋霜春露聊敬我心。”殿内供奉先祖牌位,一年四季香火不息。出正殿北耳房,进月门有一小院,转而进南小门便是后院,后院廊房为家学,后殿为族长办公视事地方。江氏族堂号为“兰陵堂”。解放后,改为青阳小学,家族象征淹没在书声琅琅中,如今这些都在记载中,眼前连一块砖头也没有了。 青阳石氏家族,至清嘉庆年间,族丁渐旺,从青阳往南一直到石集,汴河两岸姓石为最。上塘镇还有石庄。当时富户较多,古人喜欢饮水思源,孩儿有了今天都是祖上积德,于是为念祖之功德,弘扬石姓之名望,经族人公议,在青阳东圩门外(现颖都家园南门一带)置圩宅,名为石小圩,建石氏祠堂,仍取号为“乐善堂”,供奉先祖牌位,春秋祭祀。大门楹联为:“世泽於今绵泗水,家声自古振山乐。” 石氏祠堂初建时,依水而建,似有情调,可是白天砌墙,过夜就塌,一连数日,不知何故,瓦工都是石家兄弟,忠心耿耿,那究竟为什么呢?一时青阳街上“江氏祠堂、许氏楼,姓石盖的夜夜愁”顺口溜如汴河之水,流淌不息。后经风水先生察看,原来祠堂建在了神鼋的身上。移址后方才建成。 解放初期的青阳,还有那些幽深弯曲,水粉画一样的古巷,那真是宾至如归,雕梁画栋的木楼客栈,还有那精致典雅,青砖小瓦的明清商铺、庭院,那玄武湖一样的“臭河”,那青石板铺就的沿河小路,那对抱搂粗的古柳,如今都“焕然一新”了;几十年前还有名闻遐迩的老中医,威震一方的老拳师,技压群芳,名闻江淮的黄梅戏、泗州戏表演艺术家,都在今人的视野里一一消失了;就连胡耀邦都赞不绝口的青阳街空心挂面也“挂”了,那青阳北校已经超过百年历史早被遗忘,八十年前青阳海燕剧团的风采如今也没有了,一百多年前青阳喻记药店医风医德人人钦佩,八十年前青阳街第一辆英国“三枪牌”自行车也不知去向了,八十年前青阳就有了邮电代办所,七十年前皖东北第一个工人合作社就在青阳建立,还有王氏红烧肉,陈家水煎包子,老街芙蓉果、樟木果呢? 青阳街菜市是一个多彩的画卷,它从西到东,在小城老街两面排开,他的分类比图书馆学者分类精细,它的安排比法律准确而富有权威。 每天早上,老街就开始年轻生动起来,小城的摊贩从容不迫地拾掇自己的货架货物,乡下的菜农,河里的渔夫,他乡的商贩就急急往小城赶,他们带来青菜白菜,黄瓜绿豆,红萝卜,黑豆,紫苋菜,花椒,茴香;带来泥鳅黄鳝,老鳖螃蟹,黑鱼刀鳅,草虾螺丝;带来公鸡母鸭,牛肉羊腿……。 青菜青得放光,白菜白得耀眼,黄瓜嫩生生,绿豆如碧玉,红萝卜鲜亮亮,黑豆好比姑娘的眼珠……泥鳅黄鳝在翻腾吐沫,老鳖在静观其变,螃蟹在滥施淫威,做无效的挣扎,公鸡在瞠目结舌地惊恐,母鸭在嘎嘎的有一搭,无一搭地呼唤。牛肉让人垂涎欲滴,也让人感慨老牛辛劳一生也难免一刀而死,善良的小羊也逃不了人的魔掌。世界上最凶狠的绝不是猛虎恶狼毒蛇,而是人。 渐渐,小城的菜市像演出一样,道具灯光音响均以到位,演员做演出之前最后准备,把杆秤拿出来,把货物再一次调整摆好,把最好看最抢眼的货物摆在上面,自己找个地方坐下来,不怕累就站着——这也是服务态度,就等观众到来。 观众如约而至,提篮子,拎袋子,她们走走停停,不时地询问,韭菜多少钱一斤?泥鳅怎么卖的?如果回答接近自己的价格预期,就停下来做进一步砍价,讨价还价努力。这些人都是资深市民,宁砍一毛,也不多出一分,她们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理直气壮地贬低你本来很优秀的货物,使你失去要高价的物质基础,同时削弱你坚持价格的信心,说你的鱼臭了,腮都紫了,说你的牛肉是死牛肉,颜色发红了,说你的公鸡好像生瘟了,如果是没有经验的卖主,你就会被一连串的诋毁而毁,会失去自信,会节节败退,好在能来小城做买卖,基本都是老江湖,你那一套咱们经过多了,愿买不买,无奈,那些小市民就买了,成交后,临走还会多拿一根葱,一只虾,这你就不好计较了。大男人不好跟女人太认真。这些女人深懂生活之道,多占便宜,自己就可以过的滋润一点,用到军事上就是——只有有效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你从小城菜市从东向西,或反之,一路走来,萝卜青菜过了就是豆腐豆芽,再往前走就是鱼鳖虾蟹,再走就是猪肉羊肉,再走就是陈年干货,发霉上锈似得,卖这些东西的是小城的老地丁,那地盘比他花钱买的还气实,谁也别想侵占。而就是外来的也都各有地盘,这地盘是由第一次确定的,或无人使用,你使用了,或小城当地人赐给你的,总之,第一次你占下来,若有不速之客,你会理直气壮地说,上次我就在这里,你去告官,官也会说,人家上次就在那儿,你就自己再找一个地方吧。 在青阳街上,让人们记忆犹新的是街头杂烩汤。杂烩汤是马虎汤的升级版。它的锅架在菜市的尽头,静候那滚滚人流,好似在下游布置了一张大网,就等那些卖完货的人进网。 大锅敞开,热气一直蒸蒸日上,香味就是免费的广告,四处传扬,八方拉客,信者就过来,坐下,自然是不虚此行。 杂烩汤综合了人们的多种愿望,那里边有粉丝,有豆腐,有牛砸碎,有豆芽,有馓子,有油条,有油渣,还有晨星般的鸡蛋花,更为引人的是一块二斤重的五花肉,横卧锅边,被煮得油光光,胖乎乎,虽说这肉不给你吃(除了你花大价钱),但人家知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肉烂在锅里,油浸在菜里,那肉是品牌,是招牌,很多人就是冲着那块五花肉来的。 一碗杂烩汤两毛钱,厚厚实实一大碗,能吃到七八样呢,偶尔有块碎肉,细嚼慢咽,余味无穷。碗上漂着一层油花,喝一口,真过瘾,一碗下去,不尽兴,就狠狠心再来一碗,卖杂烩汤的妇人就笑容可掬,就拿你当大款,碗都放到你面前了,还再瓦半勺子汤给你,算是奖励了。两碗下肚,绿水青山带笑颜,拍拍肚子,心满意足,生活是多么美好! 那块五花肉,几天后你再来,它还在那里,在沸汤的鼓动下依然颤颤巍巍,像一个胖妇人的乳房使你心动,喝杂烩汤就是自慰了。不过比自慰实在多了。其实,至此,那块肥肉已经没有多少肉味了。近似植物了。 杂烩汤越熬越显得浓厚,里面的成分越显得丰富,喝杂烩汤的人也十分专注它的味口魅力,他们从不考虑大锅整天敞开,那一阵阵灰尘飘落在锅里,他们不去在意灰尘。只要解馋,只要过瘾。这样,杂烩汤一直畅销。 桥头杂烩汤在小城属于第一,是一个叫陈大眼的老人专门调制,人家那汤里,只是鸡蛋花星星点点,海带丝若隐若现,豆皮子三三两两,可人家用面和在汤里,好似稀饭,人家是把这汤盛到碗里以后,另外给你加佐料,酱油醋自不必说,还有胡椒粉和点滴香油,那味道,比那一锅粥式的杂烩汤味道更鲜美可口了。一度时间,男女老少,不约而同去桥头和老人的杂烩汤。大伙围着老人,端碗等候,不知情者还以为荒年时慈善机构在施粥呢。 老人死后,女儿继承,没几天,多年的老客户就不来了,哎呀,少油无盐,半生不熟,全不是老人的风味了。没几个月就停业了,女儿改做面条了。 杂烩汤虽好,父亲从不在这里享用,他总会想到表弟临终的要求。他有时想,表弟若是还在,我会买一锅给他喝,只喝得他往外冒。有一年过年,父亲连夜把一罐子杂烩汤送到表弟的坟上,给他享用。 青阳老街最顽固的贸易是老摊子,就是卖东西的摊位,多是把箩筐摆在地上交易。老摊子之老,一是那街老,沧海桑田,如今它还坐落在那里。那街多是沿河岸下,主要大街早已水泥柏油路了,这里黄土依旧。只走人,不走车,地势洼,就起名叫洼大路,哪个朝代建设都没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danhuaa.com/jdhyy/7999.html
- 上一篇文章: 荣耀之路卓越设计量身定制的精致人居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