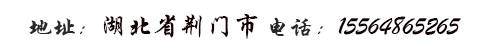最好的告别音频版
|
最快治疗白癜风的方法 http://baidianfeng.39.net/bdfby/yqyy/ 在此,特别鸣谢碰碰响女士专业的播音品质,及对支支作品的热爱。 点上面的音频按钮,播放 1. 兰卡的一月,仍是盛夏。虽是旱季,但雨水却也经常光顾。科伦坡八区。一辆白色的丰田皮卡在雨里疾驰......车上的玻璃窗将车内和车外的空间一分为二。外面的那个世界里,雨点密集般汇聚在挡风玻璃上,又迅速被雨刷器刮走,汇成两股侧流,在我眼前消失。突然“叮咚!”一声,打开手机,是母亲发来的QQ信息:“爷爷陷入持续昏迷,恐怕熬不到春天了.”我的心底像长满了苔藓,感觉被摄魂怪吸走了所有的快乐......低气压让心里堵着一面墙,我将脑袋靠在窗框,按下玻璃窗按钮,将目光投向窗外掠过栅栏......,远远的看到:茫茫雨雾里,在巨大的围木中间有一列熊熊的火......,几个僧伽罗人正在火化一具尸体,火焰里,隐约可见人形躯体的主干,仿佛正在与这个世界告别,渐行渐远.....。整个仪式只进行了一半,当地司机说,僧伽罗人去世后在墓地被火化,第二天会有专门的人来采集骨灰余烬,然后盛在陶罐里安放。 一股暗黑的力量穿透了我的胸膛,这一幕是那样的熟悉……,我想起了奶奶去世时的情景。那是儿时,一个下雪的午夜,母亲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发现家里的大人们出出进进、忙成一团。慌乱间穿好衣服,奔去瘫痪多年奶奶的房间里,她早已不在床上。最后,我在家里的水泥房殿看到她。她被放在木板上,戴着帽子,身上穿着俗艳大红的寿衣,穿着平常从来都不会穿的厚底鞋子。她被村里年长的老妪们“盛装”好停放在那里,死亡让她的身体萎缩、变小。我怔怔站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那是我第一次直面亲人的死去。十几年后,我的爷爷,又介于生死之间。时间和死亡达成了共识,它们要带走我挚亲的人。此刻我把头完全伸出窗外,仰面对天,任雨水冲刷着我在现世的三分之二。恐惧和绝望海水般淹没了我的意识,我陷入一种无可逃遁的黑暗里,看着眼前僧伽罗燃烧的尸体,心想:有一天,那具尸体会是我仍在世的亲人、朋友和自己,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那个即将赴死的人会怎么面对,留下活着的人们又怎么正确看待人将终了的事实,以至于怎么处理这具皮囊,这都是问题。我想起人生的最后一道考题就是如何面对死神的召唤。如何安顿这颗不安的灵魂,我没有答案。 2. 偶遇火化的那个黄昏,我走了很久,来到这块沙滩。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在沙滩上留下彼此交叠的脚印,看被海水洗过的每一粒沙,它们不断被涌上岸边,又被新的一轮海水在轮回中淹没 SexontheBeach 点了一杯“SexontheBeach”鸡尾酒和当地盛产的腰果,直到黄昏来临,僧伽罗人背着吉他和本国民族乐器塔姆曼达姆鼓,有时候是亚克鼓,唱着歌颂劳动人民智慧与辛勤的“矿工之歌”。 兴致阑珊时,我也会加入他们其中手足舞蹈,以此暂忘“在人间已是颠”的烦恼。 生活,日复一日。我们都在与机缘的碰撞中度过。 告别了目盲的五色,带着些微醉意,在时间的沉疴中,我沿着漫长的海岸线开始漫无目的的走。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穿过人群,一种未知的力量好似引导着我......途中遇到几个渔人抓着结实的绳索,身体和地面呈45度,嘴里喊着号子。不知走了多久,回头看来路,不见了喧嚣和霓虹,自己正在穿越一片黑暗的无人海滩,我开始奔跑。过程中遇到和我相向而行,正往西的夜跑者,彼此打了招呼,他的身影消失于夜色中。在一颗棕榈树前,我放下自己的鞋子,继续沿着涨潮的岸边跑,踩在海水刚刚淹没的沙子上,感受潮退时候那种对脚掌的微微吸力,那感觉像一个吻。突然,在海水里出现了火光,揉了揉眼睛,的确是在海水里。心想那是渔船发出来的,但是渔船不可能离岸那么近,会有搁浅的危险。我不知道好奇心是有多大的动力,于是撒腿跑过去,终于跑到了--离海岸约20米的一块巨大的岩石上,看见有一座同样是石头堆砌成的海神庙。一块块凸起不平的石块组成了歪歪扭扭的阶梯,一直通向庙里。台阶旁边的沙滩上,整整齐齐放着一双褐色的人字拖,我有点讶异。台阶的石头平滑,用脚踩上去很舒服,一蹦三跳,我就到了庙门口。果然,里面有人。是一位老者。他背对着我,双膝跪地,上肢前伸,匍匐在地,身穿纯棉纱笼,由一块长方形的布系在腰间。口中念着当地语言,在做祷告。怕惊扰了他的宁静,我躲在石庙一侧。过了一会,他从庙里走了出来,左手拿着一个莲花船一般的水灯,而右臂没有胳膊,只有空袖子在风里飘忽摇摆。他点燃灯芯,将灯座放进海水,波浪带着灯船飘飘悠悠,他目送着水灯渐行渐远,直至消失不见……。我怕惊扰了这神圣的一刻,仍旧躲在黑暗的一侧,风将我的长发吹向天际,一会又吹向海岸一侧。明月高悬,我将目光投向黑暗里万浪激荡岩石的大海。那孤单单的背影,风中胡乱飞舞的空袖筒,和站在石崖上躲在海神庙阴影里的我,在幽暗中组成了一幅看不见的画面。我以为他要走了,正准备从阴影里出来。还没有迈出第一步,发现他已到沙滩上,却并没有穿鞋,好奇心驱使我继续躲在黑暗里观察他。他面朝大海,然后用左手在兜里摸出来一个白色布包,慢慢打开来,是一大捧雪白的鸡蛋花,他将花一朵......一朵洒到海面上。 接着,他退后几步,先是向着海行了一个鞠躬礼,然后腰部下塌,两腿分开,呈半蹲状,就像蹲马步,整个动作沉稳有力。他的独臂和地面平行,平举胸前,手掌有节奏的里外翻动,动作有棱有角,头随体,眼跟手,全身和谐一致。有好几次,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里,但这位清癯的独臂老人,他就在我眼前,忘我的跳着一支舞。他带着笑容,双眼炯炯有神,一直跳一直跳......有时候,我感觉他在扮一头汲水的大象;有时候,他旋卧而坐,好似一只高傲的孔雀;快到最后,他的独臂好似掠过云端、翱翔在天际.....看着看着,我好似将自己融入了这海天一色里......他跳了大概有十幕的样子才结束,然后很绅士的向他的观众们--印度洋,弯腰敬礼答谢。然后,他提了自己的鞋子,离开了。这时候,我这个偷窥者才从庙宇的阴影里走出来,跨过已被海水淹没的石板,到达沙滩。“Miss!”一个声音从我的身后传来,我四下环顾之时,他已经站在我身边。我能更清楚的看清他的轮廓:他非常瘦,带着一副银色边框的近视眼镜,硕大的鼻子镶嵌在清癯的脸上,他嘴唇上方留有整齐的花白胡子,下巴尖瘦,耳朵像精灵那样竖着,看起来很有喜感。“我以为您走了...我...我不是故意要窥视您...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早就看到你了。”他说。“啊,什么时候?”我顿时红了脸。“我在放水灯的时候,你躲在那里,我看到你的头发被风吹乱。一开始我很警惕,在月色下,我看清楚你是个白皮肤的亚洲人,还是个女士,我就放心了。”他呵呵的笑。“噢!我不是有意打搅,只是......”他摆摆手,摇了摇头(在当地,摇头是“yes”的意思)说:"那支舞除了献给我的妻子,也献给你,我亲爱的朋友!”仿佛得了特赦般,一边往回家的方向走着,我和他攀谈起来。“您的妻子?”我环顾四周他不回答,报我以微笑。我接着问:“在沙滩上...那只舞叫什么名字?”我一边说一边用手臂比划着---一只鹰飞翔的姿势。“康提舞!源自康提地区,部落村寨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根据祈神者的舞蹈形式流传而来,里面所有动作其实都是湿婆神创造的。”“啊,圣城康提,我和朋友们去过那里!您是舞蹈老师吗?”他耸耸肩膀,眉头紧锁,但马上他又展现出笑容:“曾经是!”不知不觉,我们已走到西海岸,此时音乐隐于夜幕,海边茅屋静静矗立,身后巨浪翻滚。我们留了联系方式,道了再见。 3. 一周后,他邀请我去他家做客。那是一个别致的院落,在大厅里我看到了他夫人的遗像,海神庙见到他的那天,是他夫人的祭日。夫人以前是国家舞蹈团--ChannaUpuli的主舞,遗像旁边是她一生所得到的二十多枚奖章。“她最爱去的就是那片我跳康提舞的沙滩…,她一生都爱跳玛乌拉。那天我们一起去贾夫纳娜慰问演出的路上,我们去救路旁边一只受伤的野孔雀,没想中了反政府武装埋的炸弹,我用手臂去护她,失去了一只胳膊,但还是没有挽回她...看着最爱的人,瞳孔就那样散开,看着她很快就要告别人世的神情,我却无能无力。那天,我流尽了眼泪,努力听着她用尽全身力气,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当你跳...舞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是拍拍他的肩膀。“她走后,我经历过一段很难捱的时期。我常常思索人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而苦苦没有答案,直到想起她的话。慢慢的,我看到在内战失落的家园,那么多人无法见亲人一面就匆匆死去。而我,幸而能听到妻子讲述愿望,听到她和我说再见。”他平静的叙述着,就像这些故事的发生早已远去。“在我这个年纪,活着就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丧失”吧,丧失挚爱,同时失去了一只臂膀,我不能在以前的组织跳舞了,因为这样有损集体形象。”他顿了顿,接着说:“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度,左手被视为不洁净,但我失去了“洁净”的右手,只剩下“不洁”的左手(老人说的不洁的左手,是当地人的习俗,当地人用左手洗澡,上厕所。被视为不洁),但我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当“生命的脆弱性凸显出来”的时候,这些威胁使我重新对欲望加以排序,人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会彻底改变。我现在不怕死亡,已经失去了她,我再也没有什么好舍不得的了。”离开老人家里那天,我紧紧握着他那被世俗定为不洁的左手,我情不自禁地感到各色人的手穿越时间相握在一起。我感知到属于这历史链条中的两个环相扣在一起,而我们都漂浮在这条水流汹涌中的历史长河中。从未告别,或许,这才是最好的告别。 喜欢碰碰响的朋友,她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danhuaa.com/jdhjz/6764.html
- 上一篇文章: 六月上旬苗木清场货大集合
- 下一篇文章: 杨瑾诗歌专栏深夜闻犬吠外九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