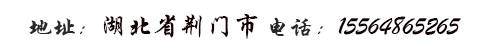今年你在哪里过年
|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哦,腊八已经过了,年已到街角,你准备好迎接姿势了吗? 图片来自网络 年的春节,除了住在武汉的人民,大部分国人都在春节前按照原计划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去了自己原计划的地方过年。至于年过得是什么滋味?答案多半是五味杂陈。只要能和家人在一起,年的春节就是圆满的。 就像一场梦,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已经来到了年的春节。从上一个春节,到这一个春节,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此刻,国人都在面临一个直抵灵魂的问题:年春节你在哪里过年,和谁一起过年? 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不难回答。年政府倡导我们都留在原地过年。非必要不出境!好的,我们不回马来西亚了。非必要不出京!好的,我们不回老家了。这么配合吗?是的,就是这么配合。有什么理由不配合呢? 第一,回马来西亚。几番核酸检测,入境马来西亚隔离14天,和爱人执手泪眼相看。爱人说:“Darling,let’sgohome.”“No,darling.It’stimetogoback.” 都来不及进一步深入亲热,就得挥手说拜拜,直接回国继续隔离14+7天,彼时学校已开学1周。出境不考虑! 图片来自网络 第二,回老家。即使你拿着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村长也并不想让你回。村长说你就在那头吧,别回来了,不行我再给你发个红包。 咱不差这个红包钱,一腔热血回去了。到了村头,村长说:“这里有个还没扒的土屋,你在这里先隔离几天再回你家。” 我每天看着四处溜达的鸡鸭猪狗,对着广阔的田野思考人生,还得搭上老母亲每天给我做饭送饭的辛劳。出京不考虑! 图片来自网络 今年我要留在北京过年了。42年的人生里,在北京学习生活的年头有25年,这也才是我第二次在北京过年。 第一次是年春节。结婚第一年,娃还在肚子里7个月左右。身怀六甲,出行不易,就干脆留在北京过年吧。虽说也是我和儿子在北京,但是还在肚子里的他尚不知年为何物。 母亲怕我孤单,派了二姐母女两个人来陪我过年。那是第一次不在父母身边,不在家乡过春节。没有了过年的喧闹,没有了帮着家人准备年货的跑前忙后,也没有了大年初一早早起床第一个给父母磕头拜年拿压岁钱的兴奋。 但是那也是我第一次要做母亲了,过完年娃娃就要呱呱落地了,那个年充满了对新生的期待,对未来的向往。 今年留在北京,往小了说,是不给政府各疫情防控部门增加压力;往大了说,是对生命的尊重;往明白了说,那就是怂,的确害怕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 既留之则安之。生活不能没有仪式感,就算只有我们俩也要把年过得有模有样。哦,不对,还有阿姨。阿姨今年也不回老家,留在我家住家了,今年我们三个人一起过大年。待我来仔细规划一下。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这些老北京的传统,我们就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来操作。且这些都属于阿姨的主权范围,我们俩就负责围观,掺合和享受劳动成果吧! 过年,我心里有几件最重要的事要一定要做。 第一,把过年的新衣准备好。 小时候过年,最期盼的除了有好吃的,就是大年初一穿新衣服。母亲一定会给我们姐妹三个准备三套新衣服,不管是亲手缝制还是买回来的,款式绝对引领我村乃至我县时尚。 大年初一之前,衣服是放在妈妈的大木箱子里的,拿出来时衣服自带一股清新的木香,那是年的味道。大年三十晚上临睡前,就把新衣服平平整整地放在两层被子的中间(老家冷,春节那会儿都得盖两层被子。衣服放在中间,第二天早上衣服上身是温温的)。早上起来,先闻闻那个香,再美美地穿上,能从年初美到年尾。 我没有我娘的巧手,这个节骨眼上也不能逛商场,就只能淘宝解决一切,希望也能美一年。 第二,准备大年三十要贴的春联。 我小的时候,大年三十早上,我最喜欢干的活就是把去年的春联揭下来。那会儿的门都是木门,带有岁月痕迹的木门。对联是用妈妈熬的面糊糊贴上去的,一年贴一年,没有哪年彻底揭干净过,每年揭的时候还都能带下来硬硬的往年的春联碎片。 我爸爸认字不多,偏偏喜欢写打油诗,韵脚压得很好,每次都能从诗里找出一两个错别字。但是他字写得甚好,每年都是爸爸自己写春联。家里的大方桌拉出来,铺纸研墨,我就旁边候着。爸爸写好一张,我就拿走一张,摊在旁边晾上。 三十早上,在春联上刷上还带着温度的糊糊,张贴在大门、二门、偏屋门上,猪圈、鸡窝、牛棚上。后来我们长大了,爸爸退居二线,我二姐夫接下来这个光荣的任务。二姐夫是教师,文艺青年一枚,文采和书法俱佳。我的工作也被小一辈接替了。 如今,我家少年已经可以挥毫泼墨。去年家里贴的就是儿子写的“福”字。为了让这个福字有足够的分量,我们门上只贴了这一张“福”字。字写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继承了这个传统,担起了家里的一份责任。 今年,我也准备好纸墨笔砚,等儿子来完成这个春节传统。 第三,大年初一早上,6点起床,穿上新衣吃扁食。 在老家的时候,初一早上,天不亮我们就要起来吃农历新年的第一顿餐:扁食(韭菜鸡蛋馅素饺子)。 吃扁食要就着葱和蒜吃。吃素饺一年头脑都不昏(同“荤”),吃葱聪明一年,吃蒜会算账,这是一年最经济又实际的愿望。 早上这顿饭由家里的男人煮。女人围着锅台转了一年了,这一顿就坐着等吃。我们家早起做饭的肯定是我爸爸,后来是我二姐夫。虽然他们要做的就是把水烧开,再把扁食放到水里煮熟,但是对于家里的主妇来说,也是个聊胜于无的安慰。 今年在北京,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儿子责无旁贷,我就准备坐等少年煮好扁食端饭上桌了。 图片来自网络 第四,初一早上吃完饭,给老爸老妈视频拜年。我很小的时候,村里有喜欢守夜的,过了12点,一点多才放关门(鞭)炮睡觉。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人起床开门放开门(鞭)炮了。鞭炮声一整夜“噼里啪啦”,此起彼落,连绵不断,大公鸡们也不知道啥时候该睡觉,啥时候该打鸣,它们也跟着“喔喔喔”,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村里前前后后3、4点钟就都起来了。大家各自在家吃完扁食,就开始左邻右舍,走街串巷去拜年,近门远门都拜,走着走着就能串好长一个队伍。 长辈准备好压岁钱,晚辈给长辈磕头,磕完就能拿到压岁钱。一早上挣得压岁钱都是一个头一个头嗑出来的。每次拜完年我就和姐姐们比谁的压岁钱多。我是我家最小的,每年压岁钱也属我最多。 后来大家就睡到5,6点钟才起床,拜年也不真磕头了,但是压岁钱还是照样给,数额也越来越大。再后来大家就更随意了,有7、8点钟起的,有熬夜太晚不起床的。拜年也不一家一家走了,特别近的就去拜一下,远门的就压根不去了。 今年我们在北京过年,“初一初二满街走”的传统还保留吗?邻里没有走动,朋友们都住得很远,还走吗?走!我准备开着车带着儿子走北京,沿途走到哪个朋友家就去哪个朋友家拜个年。不聚餐,不逗留,鞠躬作揖送祝福:“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初一初二会到哪家拜年呢?留个悬念,敬请期待。 图片来自网络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danhuaa.com/jdhjz/5813.html
- 上一篇文章: 山中一草炒成茶,保健功能不容小觑
- 下一篇文章: 春季西安周边观赏油菜花攻略,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