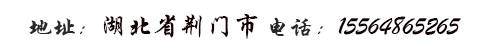思华年鸡蛋花与龙舟雨忆敬爱的老师们
|
级德语张晓露 作为大学教师,我已经工作了整整五个年头。我常和我的学生提起我的大学,我的老师们。有一天有个学生问我:“老师,中大真的那么好吗?是不是因为你最美好的青春在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度过了,所以母校和你的老师们在记忆中才这样地美好?”我说:“不,是因为母校这样的美好,是因为我的老师们,我才有我最美好的青春。” 从年入学读本科到年研究生毕业,老师们看着19岁的我从一个少女长成了一名人民教师。治学、教学、为人,从他们那里总是有学不完的东西。回忆起老师们来,总是有说不完的故事。 细长眼睛的曾老师 曾老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潮汕男人。班上有一个特别时髦的女同学,发型穿着总是变着样子。有一天听见曾老师大吃一惊的声音:张同学你怎么了?眼睛怎么变成紫色了?!她解释说是带了变色瞳片,曾老师松了口气说:没事就好。还是这位张同学,头几天披着大长发,没过几天变成清汤挂面学生头,又过几天发型是染成银色的极短发。对当时临近退休的曾老师每天都构成审美刺激后,她披着大直发又出现了。大家都看到曾老师那天明显惊呆了。由长变短好解释,怎么从板寸头又成了大长发?!原来她是戴着不同的假发出现,曾老师幽默地笑着说,这倒方便,不用总为发型操心。 就我记忆所及,曾老师从没有批评过哪位同学。我们当时在寂寥的珠海校区读大一大二,刚接触到德语学习,过剩的荷尔蒙加上全新的生活和学习环境,那会儿的我们必然是一群让人头痛的大孩子。就像他饶有趣味地接受并欣赏了张同学的各种“时髦”一样,对待学习上的各种问题,他也总是先理解后鼓励,用各种方式鼓励我们在枯燥的语法课上活泼一些,比如让我们看德国风光明信片,向我们赠送原文字典等。 他笑起来眼睛更加细长,眼角的纹路也总透着幽默和智慧。毕业好几年后,我们去拜访已退休的曾老师,我说:“曾老师,您一定不记得我啦!”他又是那样一笑:“你是来自福建的张同学,你以前是搞杂志社的嘛。”在场的同学都惊呆了。于是我们给他做了好多测试,每个同学的很多细节他都记得。大家惊呼:“您怎么都知道啊?”他又幽默地笑着说:“我在学校里可是有小广播和视频眼线的!”笑里竟透着一丝顽皮。 很美的王老师 王老师是一位在课堂上课堂外都能渗透美和知识的教师。 有一天,有个同学在教室里放德国国歌官方版本,恢弘的管弦乐加上浑厚的大合唱,可大家都嫌不好听。王老师说:海顿的乐曲,怎么会不好听呢?德国国歌很好听的。她接着清唱了一小节:EinigkeitundRechtundFreiheit,fürdasdeutscheVaterland…她的这个国歌版本是我所听到过的最动听的德国国歌。 到了夏天每天都有一场暴雨,必定是在下午的文学课前。鸡蛋花落了一地,我总是不忍,拾起几朵,有时与同学一起别在头发里。王老师见了就说:“这样太美了,昂山素季总是别着这种花儿。”于是我们就会送她一朵,她特别喜欢。 读到大三,语言学习的挫折日益增大,课堂上似乎陷入了某种对德语的普遍沉默。王老师在文学课上讲Eichendorf的一首诗,她慢慢地念着,陶醉地说:“你们看,这个词、这个句子多么的美妙!德语多美啊!”讲台下报以毫无体会的茫然表情。她笑着说:“你们该放松一点,从语法的纠错当中走出来,慢慢去体会语言的美妙之处。”当时的我,确实是体会不到德语的美,但她的神情、语气是那样地有说服力,于是我也期待有一天能领会到语言的美。 学院组织教工们跳古典舞,她在办公室里给我演示:“古典舞简单,你看,古典舞是讲究对称和追求完满的,你一手从这出去,这一边肯定得退回来,这样一来一回这个动作就很完满。”到现在我仍能清晰地回想起她看手的那个眼神,脚上的那个动作,是那样的美。她说:你看,把这些动作概括起来,找出规律,就不那么难了,而且能从中体会到它的美和乐趣。 考上本系研究生后,我报名参加团中央的“西部计划”支教团。当时身边反对的意见很多,一位师姐非常诚挚地跟我说:“这当然是件好事,但语言学习的中断不可避免会影响你在专业方面的深造。”和王老师谈这件事时,她月牙般的眼睛一下子闪亮起来:“那太好了呀!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真是再好不过了!”她和我深入地谈了好久,谈理想与学业,谈舍与得。在支教的那一年里,王老师与我常常通电话,几乎不会发短信的她也学着常给我发短信。那年的中秋节,她给我邮寄了几盒“美心”月饼。我和学生们痛痛快快地过了次奢侈的中秋节。她将家里的童书和童衣都收拾好寄给我,请我发给孩子们,还交代我说,要暗地里赠送,以保护孩子们的自尊心。 在我的小世界里,她就是最美的老师。 超有爱的彭老师 彭老师是很爱自己的学生,很“护短”的老师。她总是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欣赏自己的学生。 我们有个师弟,上课总是打瞌睡,课堂表现一般。和彭老师谈到他的时候,彭老师说:“他很有想法,或许上课不积极,但他对自己的理想很坚持,我欣赏这种对自我有清晰认知的人。”几年后,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这位师弟在非洲编撰了第一部当地语言的中译词典,深感彭老师没有拿一般的眼光去看待这位师弟真是太有先见之明。 一次寒假后开学回校,我见她黑了不少,就问她:“彭老师这是上哪儿度假啦?”她特别高兴:“哎呀还是我的学生有眼力劲儿,别人都说我气色不好呢!这几年德语没白学啊,德国人喜欢度假变黑,你是学进去了!” 五月的时候广州总是下雨,我们常会抱怨阴雨烦人,她笑眯眯地说:“这是在下龙舟水,为划龙舟做准备呢。”打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抱怨那时候的雨了,彭老师的解读真的让人充满了期待。 读了研究生后,被告知称呼“X老师”非常地不学术,而应该代之以“X博士”或“X教授”。我们几个想了想,跑去问彭老师是否以后要不一样地称呼她。她抬手捂着嘴笑了,说:“要是在德国,可得把头衔都叫完,将学位和职称都得叫上,如果对方有双博士学位,就得称呼ProfessorDoktorDoktorX,还没叫完对方应该已经走远了吧!但是无论有什么样的学位和职称,本身不就是教师吗?你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地叫我吧!” 读研的时候在彭老师的课上学习翻译理论。那时的我们看得一知半解地便在课上大抒见解,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不好意思,很多想法非常幼稚,看了一点皮毛便觉得自己观点独特。但彭老师总是认真地听,沉思后一般会给予肯定,然后再相应地提出问题,让我们接着讨论,从没有说过“这是没看懂”这样的话。在她的课上,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的观点或角度并不肤浅,Seminar这样的讨论课总是上得意犹未尽。 学院很重视我的支教经历,因此研究生入学典礼上让我作为新生代表发言。会后彭老师眉飞色舞地说:“看!这就是我们德语的学生,有想法,与众不同!哎呀,我们德语系今天太‘威水’了,我坐在下面真是太骄傲了!”本来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心得,但看彭老师这样快乐的样子,自己也稍微地得意起来了:彭老师把我看作德语系之光呢! 彭老师将自己和学生看成平等的个体,欣赏学生不同的方面。她会和我们讨论饰品、美食,介绍我们认识Bauhaus家具,谈论家庭观念等等。通过她看待学生的方式,我似乎也学会了如何更平和更全面地去看待别人。 我们敦厚的程老师,认真的林老师,很酷的凌老师,风趣的冯老师等等,还有学院各位行政老师,在我的中大求学期间,包容了我许许多多幼稚的错误和言论,总是微笑着在各方面帮助我,每每想起他们,内心都充满了感激。限于篇幅,在记忆中挑拣出来写在这里的只是几位老师的几件小事。还有一些,我藏在记忆深处,常常回想,根本舍不得写出来分享,比如王老师轻轻叹一口气我能怕几年,修辞学让我们失眠了半年这样的事情我肯定是不会写出来的。还有一些是老师们和我的秘密,老师们的善言善行,基于老师们低调的为人,我们之间说好了不写出来的。 在中大的六年里,老师们用自己的言行一点一滴地教授了美的感受力,幽默的生活观,宽容开放的人格,严谨的治学和宽厚的为人。老师们的人格魅力融入了学科知识,我在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的成长因此变得完整、健康。我时常鞭策自己要像我的几位老师一样温暖、磊落地为人为师,他们的言行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使我成为更美好的人。虽然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常常为自己及不上各位老师的一分一毫而感到失落或受挫,但我想他们几位一定是笑着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会更加好的。 这样一想,因为有了亲爱的老师们,就有了继续前行的勇气。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feizhouxiangdx.com/jdhjz/1313.html
- 上一篇文章: 中国这20种饮茶习俗,你知道几种
- 下一篇文章: 农村这种植物我们叫它鸡蛋花用它来消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