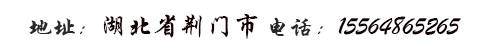你家宝宝开启复读机模式了吗
|
1 “熔岩!” 天气渐冷,我收拾出铭亮换季的衣服,放在太阳底下暴晒,等到晚上把衣服一起堆在沙发上,整个客厅都是浓浓的太阳味儿。铭铭、亮亮和我挤在沙发上的衣服堆里,聚精会神的看一部关于海岛的纪录片。 纪录片的导演肯定是个对颜色颇有追求的人,他用镜头摄取自然界里最纯粹的色彩:深黑的宇宙、水蓝的地球、纯白的云团、蔚蓝的大海、碧绿的森林。直到屏幕上出现了火红的熔岩在跳跃、翻滚,铭铭突然激动的大叫:“妈妈,看!熔岩!熔岩!” 他最近正迷上火山,对于我所描述的熔岩非常着迷却又无法施展想象,终于在电视上看到熔岩的真身,所以异常兴奋。 “哇,是哎,熔岩!快看!”我假装出和他一样很感兴趣的样子,不至于扫了他的兴。 亮亮本来一直窝坐在衣服堆里,瞪着眼睛,默不作声。他大概看不懂电视上说的什么,也不懂哥哥和妈妈突然兴奋着什么,但是不甘心被落下,于是立即问了一句:“什吗?” “熔岩!”我仔细的告诉他。 “yan,yan,yan”亮亮边学着发音,边开心的笑。 亮亮学了一半,还拖着长长的尾音,听起来像模像样的,逗得我和铭铭也一起哈哈大笑,只是这笑声还留了点尾巴没收住,亮亮即转过身歪着头看我,手指着电视:“什吗?” “熔岩”我慢慢说,力求咬字清晰。 “ongyan,ongyan”亮亮也努力重复。 看他笨嘴拙舌的学话,可爱极的样子,我忍不住刚把笑挂上嘴边,亮亮又问了。 “什吗?什吗?” “熔岩,熔岩,熔岩”我一口气讲了几遍,好让他记住。 “longyan,longyan,longyan…”他跟着了魔似的念个不停。 “亮亮你是复读机么?”我开他玩笑。转念一想,他们这代人肯定连复读机这老古董是什么都不知道了,真是自讨没趣。 谁知“么”字还没从嘴巴里溜走,亮亮又昂起小脑袋大叫:“妈妈,什吗?什吗?什吗?” 我几乎要哭笑不得了,还好此时画面一转,从火红的熔岩变成了长相怪异的海鬣蜥。亮亮立马闭嘴了,目不转睛的盯着电视上丑陋的海鬣蜥。 “妈妈,这是什么?”铭铭立马问。 “海鬣蜥啊!”还好此时电视上打出了字幕,及时拯救了一无所知的我。 紧接着旁边就响起带着口水、黏黏糊糊的声音:“什吗?什吗?” “海鬣蜥!” “xi,xi,xi”大概这个“xi”的音又给他带来新的乐趣,说个不停。 隔了5秒,亮亮又叫:“什吗?什吗?什吗!” “海鬣蜥、海鬣蜥、海鬣蜥。。。”我的声音逐渐拔高,还带上了点不耐烦,可是亮亮怎么懂得分辨大人的语气来揣测大人的心情呢!他只管问,每隔5-10秒,问一次,我若回答得迟缓了,他便自动把音量跳高,那尖尖细细的童音甚至能盖过纪录片里的讲解员,让我不得忽视。 所以我干脆就盯着亮亮,专心的等着他来问吧。他一回头正巧撞上我等待的目光,大概觉得是我在跟他玩游戏,立即笑成一朵花,当然嘴里也不忘记问:“妈妈,什吗?” “海——鬣——蜥!” “laxi”亮亮这次多发了一个音,虽然“lie”发不出来,但是也是小小的进步,他得意的颠过来到过去的念,好似绝不会厌烦似的。 于是,这一个晚上我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无数遍。 如果对象是和我一样的成年人,将谈话重复了两遍,大概就已经很不耐烦了,要么大吼一声“你听不见么!”,要么无奈的放弃“算了,不说了!”。如果是面对孩童,多数人则能多生出几分耐心,将其视为孩童天真的表现,或者自动就把原因归结到小孩心智发育不完全,所以早早谅解了。那再如果对象变成了眼花耳背的老人,不知道人的耐心又会变成什么样了。 2 “那是什么花?” 夜里,铭亮躺在我左右,轻轻的呼吸拂过我脸颊,温热得发痒。我想起在巴厘岛旅游时,导游阿伦说了一个自己经历的故事。 阿伦说,他曾经带过一个“千岁团”,也就是说团里的成员,年纪加起来有一千多岁了。阿伦带着他们在巴厘岛玩了五天。第一天去宾馆接团,一个70多岁的老伯指着花园里树上的花问:“阿伦,这个是什么花?” “是鸡蛋花,巴厘岛的岛花,这里到处都是这种花。”阿伦热情解说。 “为什么叫鸡蛋花?”老人很好学,继续问。 “因为这里中国人来的多了,认为这个花很漂亮,好像打出来的鸡蛋,中间黄黄的像蛋黄,四周白白的像蛋白,就叫它鸡蛋花,后来喊的人多了就这么喊下来了。”阿伦当作一个小故事,讲的很生动。 千岁团都上了车,启程去往海神庙,老伯正好坐在阿伦身边。大巴在拥堵的街头缓行没多久,老伯拍拍阿伦的手说:“阿伦,你看这马路上的是什么花?” 阿伦伸脖一看,还是鸡蛋花,猜想难不成是老伯考验他,因为经常遇到年纪大的老伯却很顽皮。“是鸡蛋花,老伯!” “那为什么叫鸡蛋花?”老伯像准备好了似的接着问。 “因为来这里的中国人觉得花很漂亮像鸡蛋一样,中间黄的四周白的,所以叫它鸡蛋花,叫的人多了就这么叫下去了。”阿伦耐心的解释。 阿伦等着老伯还有什么问题,结果什么都没有,老伯坦然的继续看窗外。 大巴驶出城,窄小的双车道两边生长着一丛丛形态各异的鸡蛋花树,甚是好看。 “阿伦,这是什么花?”老伯又转身问阿伦。 “鸡蛋花!”阿伦只得继续回答。 “为什么叫鸡蛋花?” “因为中国人觉得这个花中间黄黄的像鸡蛋一样,就叫它鸡蛋花。” 阿伦说,后来在五天的行程中,这位老伯每天都要问十几遍这样的问题。刚刚问完,点头说谢谢,车子开到下一个景点,看到一棵鸡蛋花树,老伯便又问一次。听阿伦这样说,我们团里的人都笑开了,笑这老伯痴,笑阿伦被迫一遍遍重复的无奈,阿伦也和我们一起笑,这大概对于他是很有意思的回忆。 阿伦继续说:老伯记性不好,前面问的马上又忘记了。老伯这样一遍遍问,不要不耐烦,这不就和小宝宝不停的问“妈妈,这是什么?”一样么。你肯定不会生小宝宝的气,会一遍遍的和宝宝说。这些老伯年纪大了也是一样的,不要嫌烦,他们就和宝宝一样嘛! 于是这个操着一口广东普通话,瘦高的像竹竿一样的导游,在我紧张的记忆里,占了一席之地。 怀里的铭亮都睡熟了。我轻轻的许下两个愿望:愿我老的时候记忆不要消退的太快;愿我们都能耐心回答彼此的问题,即使是千千万万遍!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feizhouxiangdx.com/jdhjz/1264.html
- 上一篇文章: 多肉科普常见冬型种夏型种春秋型种分类
- 下一篇文章: 旅行逗比之家行走推荐世界上第一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