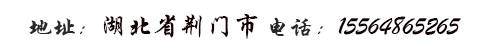咪咪妈妈手记两座墓
|
七八月之交,咪咪妈妈因单位培训,有机会在苏杭流连。工作之余,在号称天堂的苏杭走了几步,之前又曾去了粤澳两地“南寻”,因此想在这里写下一路上的点滴印象。 我要写的,是两个墓。 咪妈的旅游口味与众不同,老喜欢往墓地跑,而拜谒历史名人墓地亦常能带给咪妈灵感。 好多年前在湘西凤凰,到沱江畔听涛山沈从文先生的墓地时,其简朴深邃令我极为感动。感动之余,博士论文就专注于研究土匪题材文学了。 后来在新英格兰访学,拜谒了容闳先生的异国之墓后极受震动,就循着他的人生道路、历史轨迹写出了一本书(即将出版)。 是的,咪咪妈妈非为看墓而来,而是为了墓中人,想要与仰慕的人隔着时空对晤。 盛世太平,人们习于安稳庸常的时代,往往也是产不出思想、文化超人的时代。要寻找英雄,只好穿越到过去。只不过历史的星空群星闪耀,不可能和那些了不起的前贤一一建立联结。偏偏想去拜谒某人,不过是因了一份与自己的生命经历擦出的火花,存了一份刚好遇见的感动,读过他们的书,知道他们的功业,追慕他们的情怀。虽眼不能亲见其人,耳不能亲听其示训,但在墓前怀想前贤往事,敬畏他们向死而生的勇气,心中便会生出虔敬与感动——这也是一种交流,看不见的能量交流,我谓之为“心视”,为“神交”。 每每当我走过他们的墓地时,仿佛感觉从他们的精神和灵魂里穿越而过,而之后的我已非昨日之我。 最近拜谒的这两座墓依然给了我一生无法忘怀的印象。 *罗伯特·马礼逊之墓 一是在澳门基督教坟场旧址里寻到的罗伯特·马礼逊之墓。 任何对十九世纪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马礼逊博士这个名字。因为他是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 年前,年9月的一个黄昏,这个英国青年自澳门风景如画的南湾登陆中国,在此后长逾1/4世纪的岁月里,他克服各种困难和挫折,致力于在华传播基督教福音,直到年因病辞世,在中国土地上为了自己的信仰服务了27年。 不过说起来,他的传教成绩实在拿不出手,他用了整整27年的时间,一共只为上帝收获了四名中国信徒,其中还只有一个人留下来协助他传教,其他人难说是不是最终反悔,跟上帝拜拜了。因此在传教这件事上,他可说不上是人生赢家。 但另一方面,马礼逊却非常笃定自己在做一项巨大的事业,那就是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开拓者,扮演了摆渡人的角色。他编撰了世界上第一部汉英双语字典《华英字典》,19世纪首次将圣经译成中文,在中国首创了近代中英文报刊,第一个在中国设立了中西医结合的医馆。他为封闭在铁屋子里而不自知的人们,轻轻地悄无声息地将窗子松开了一道缝隙。 身为英国人的他,远渡重洋,奔赴他乡,死于异国,最后被葬于今天的澳门。 至于我之所以众里寻他千百度,跑到赌场王国去找他的墓的缘起,说起来简直就是半部近代史了。 这样说吧,当年因为马礼逊博士只身在中国传教缺少助手,从而有了年美国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裨治文的到来。马礼逊因积劳成疾去世后,为了纪念他,也继承他从事文化教育传播的遗志,裨治文在来华外商侨民中发起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而这个机构创立了一所马礼逊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其办校宗旨在于“使本地(指中国)学童,在他们自己的学校中,学习英文,通过这项媒介,使他们进而得以探求西方的各种知识”(《中国幼童留美史》)。 不过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一心想读的是圣贤书,考科举走仕途,对于让孩子了解西方毫无兴趣,这就给了几个穷孩子以受西方教育的机会。这最早的一批学生仅有不多的五六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 容闳后来又跟随马礼逊学校校长勃郎博士到了美国新英格兰接受教育,并考上了耶鲁大学。之后学成回国,经过18年的执着努力,促成了一件中国前所未有的创举——年大清帝国派遣留美幼童名到美国接受西方教育,从此开启了近代中国官方留学历史,而这些留美幼童中不少人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各项事业的开拓者。 显然容闳是这段历史中重要的节点人物,而要深入认识容闳何以成为历史上的容闳,自然要从马礼逊这里开始追溯。这就是对中西文化交流历史有兴趣的我为何想去拜谒马礼逊之墓的缘由。 那天和丹早早起床,吃完早餐,从繁华拥挤的澳门标志性名胜地大三巴旁边穿过,来到了基督教坟场旧址所在位置。正好下了一场大雨,我们只好在附近的白鸽巢公园里的茅亭里躲雨。丹说台风要来了,所以雨多,但来得快去得也快。 真的,很快便雨收云住,风和日丽,从公园出来,目的地就在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门上写着“圣公会马礼逊堂”,门边有“澳门历史城区基督教墓园”的介绍。小门里面极其安静,没有一个人,与外面的繁华世界形成有趣的对照。墙里面静静矗立着一座简朴无华的基督教堂。 基督教堂与天主教堂很好区别,外形上天主教堂华丽雍容,装饰讲究;基督教堂则简朴无华,素净之中自有肃穆之感。教堂旁边是一个坡。往坡下一眼望去,数株高大的绿树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园子,这是一片石碑和石棺林立分布的旧坟场。虽是墓地,却绿草丛生,没有丝毫阴森,有的只是安详静穆。西方人墓地往往如此,肃穆方正,呈现出一种安宁气氛。 墙外是熙熙攘攘的生,墙内是安详宁静的死,这种奇异的比照令我觉生无那么重要,死也没有那么可怖。雨后阳光在湿润的空气里轻俏地跳舞,有鸟儿在树间婉转歌喉,间或有一两朵白色的茶盅大的花儿从高高的树桠间无声无息地掉落,先是落在石碑上,最后掉入草丛间。 看着这一片石碑和石棺组成的安静世界,我有些恍惚。 丹告诉我落在地上的花是鸡蛋花,名字很接地气,花却淡雅大方,散落在草地间,为静谧安宁的墓地平添了几分诗意。我在草地上来回走了几趟,努力辨识石碑上的名字,却始终找不到罗伯特马礼逊的墓碑。 丹站在入口处,远远看着在墓间穿行、走来走去的我。我们如同分别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不要她过来。 最后,我终于在入口边不远的墙角边,找到马礼逊的墓,并他妻子的墓。原来,我想错了。我设想如此有名的传教士,必然会有大型的纪念石碑,所以找的时候注意力全放在那些华美大型的纪念碑上。 我错了。马礼逊的墓就靠着墙边角落,一个极其朴素的置于地面的石棺。石棺没有任何特出的地方,上面刻了数行英文,述写了马礼逊一生最重要的业绩,第一句便是: 纪念 罗伯特·马礼逊 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 (罗伯特·马礼逊之墓) 在石棺的左下方,不知是谁,放了几朵白色的鸡蛋花,柔美新鲜的花朵,与泛起了青苔的灰黑色石棺的静穆沧桑恰成动人的对照,可以想见以花朵致敬马礼逊博士的人是知道那段历史的,因为全墓园里只有这个石棺上放了花儿。我和丹都捡拾了一朵鸡蛋花,放入其间,表达我们对墓中人的敬意。 我忍不住用手指一个一个字地触摸着那些铭刻在石棺上的字母,那些沉重的字母传递给我一种奇特的交响乐般宏大庄严的触感。 我想,人的一生当然是很短暂的,但为了自己内心的信念而耕耘一生,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一定是安宁喜悦的,睿智伟大之精神,不需要万人瞻仰,而自有其永恒价值。 从马礼逊之墓,我既看到他的永恒的谦逊,也看到他的永恒的骄傲。 *和靖先生之墓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宋·林逋《山园小梅》 一看这首诗就知道,我要说的第二座墓是北宋林和靖之墓。 林逋(-),字君复,后人称和靖先生。《山园小梅》是其咏梅的千古绝唱。 梅妻鹤子的林和靖,往日只是在这疏影暗香的绝美意象里惊艳他的才华,直到年的8月4日,才有机会来到西湖之畔,来到和靖先生墓前。这里要谢谢带我们深度人文游的最佳西湖向导小哲了。 和靖先生没有让我失望,诗句之外的相遇让我又有另一种惊艳。 《宋史》卷四五七: “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一说奉化黄贤人)。少孤,力学,不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闻其名,赐粟帛,诏长吏岁时劳问。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庐,清谈终日而去。尝自为墓于其庐侧。临终为诗,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之句。既卒,州为上闻,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赙粟帛。……逋不娶,无子,教兄子宥,登进士甲科。宥子大年,颇介洁自喜,英宗时,为侍御史,连被台移出治狱,拒不肯行,为中丞唐介所奏,降知蕲州,卒于官。” 历史中的林和靖,一看就是一副道家清和冲淡的模样。他一辈子不娶妻,也不当官。一辈子不结婚的女子,人们称之为“处女”,一辈子不当官的读书人,便称为“处士”了。林和靖堪称“北宋处士第一人”,他不仅不出仕,而且只在西湖边吟诗作画,种梅养鹤。 据说童子放鹤时,西湖泛舟的他便知有客人来访,好掉转船头回家招待客人,放在今天实在是奢华到了极致的风雅。他提前在湖边为自己修好坟墓,并写了一首这样的绝命诗: 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头秋色亦萧疏。 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 ——林逋《自作寿堂因书一绝以志之》 诗中他为自己一生作结,欣慰尚有湖光山色陪伴于坟头,而一辈子自己并没有折节趋利谄媚过权力。处江湖之远,活得却分外地清明,生命的热情化作那一缕梅魂,在历史深处暗香浮动。 那天傍晚,小哲带我和同事巧从西湖边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游览到文澜阁,再到西泠印社,秋瑾墓,然后来到林和靖墓。 墓地背靠孤山,面对西湖,只见夕阳如金,洒在泛起微微涟漪的湖面,风送荷香,有水鸟闲闲立于露出水面的木桩上,如诗如画。 绿树浓荫下,我们上了几重台阶,见放鹤亭,旁边便是放鹤台了。台地靠山处便是林和靖墓。墓地外面有墙,如同一座小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小门。进到门里,可见一座黑土堆砌的高坟立于台阶之上,周围砌有石砖,坟前有灰白色石碑,书有: “林和靖处士之墓” 碑前置放着一个古朴的石制香案。土坟面向西湖,一派浑然素朴,高坟四周植梅数株,衬得坟墓极其雅洁清正,突然地,这素朴静雅冲淡风格让我想起宋朝雨过天青色的汝窑瓷。人的精神人格风骨之美,与物的颜色气味质地之形式美竟然相通。只不过美的本质的获得,前提是必须真实无伪。不然站在墓前的我也无从真实感受到这种美,无论是以眼观,还是以心视。 我在和靖先生墓前,浮想联翩。想着待到冬天梅花开时,一定要再来拜谒一次。那时白雪里盛开的岂止是梅花,浮动的又何止有梅香?与和靖先生隔着时空,对晤赏梅,定是生平不能错过的相逢。因着他和这墓地,令我对于传统文化的动人之处,有了更丰富的感受。 要说,我造访的两位过去的名人,处于不同时空,罗伯特·马礼逊博士为了信仰而奉献一生,林和靖先生为了洁身自好而选择在西湖放逐自己一生。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点,甚至有些背道而驰,前者是有所为,后者是有所不为。 但仔细想想,他们之人生选择,为或者不为,深层却有着相似的出发点——那就是绝不背叛自己的生命之真实,为了实现生命之真实,愿意为信仰远涉重洋去往异国、面对各种艰难挫折;也宁愿江湖泛舟,承受无法实现自我之社会价值的寂寞孤独。 其实古往今来的哲人智者,能在时间的大浪淘沙中熠熠生辉者,大抵都活出了生命之真实。因为如果连面对自我生命的真诚都没有,又如何能够把握世界的真实。 今天的时代,种种现象不是证明了,如果缺少面对真实的勇气,越奋力往前,离岸便越远吗? 年8月12日凌晨咪咪妈妈记 参考: 1、美·勒法吉《中国幼童留美史》,珠海出版社。 2、《马礼逊文集》,大象出版社。 3、百度词条:林和靖 咪咪妈妈,职业为师,文学博士,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danhuaa.com/jdhwh/4863.html
- 上一篇文章: 给你三秒说出校徽含义,你跟我说不记得它长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